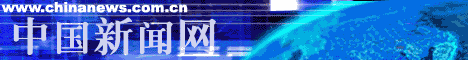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———�����еĶ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߰˸��ס��е�Ĩ�����촽———Ů���߰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Ů���ң���Ҳ�ܸ����Լ���Ů���³����ʽ��չʾ�ߡ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ļ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εĻ���ʻ��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ǰ���桶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Ժ��ֳ����߰˱��飬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侲��ѧ��———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ѧϵ��ѧ����ʶ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걾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ѧ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֪ʶ���Ӽ�ͥ�����ĵ��̺ͼ�ʮ���й���ͳ��ѬȾ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ܵķ��С�����쵽�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Ȱ�ķ���———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ʻ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³��Dz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߷緶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顶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Ȿ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鲻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ӳ��Щ�ܷ��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Щ�ˣ�ҪΪ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ߵij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ɷ���4000���й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ˮһ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İ칫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һ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ˡ�Ц�ˣ����Ƿ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ӵ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Ѽ���ͬ�±��ܣ�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�к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˰��ٵĹ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ٵİ���Ͱ��ٵ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Ƕ���ʱ�е�һ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ļ�¼�߰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ࡱ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û��ͨ�����ǵĿ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ɷõ�Ů���Ӷ�Ҫ���ң��㿴���IJ��վ磬ϲ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û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һҹ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Ϸ�ʵس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ࡱʱ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ࡱ����ʵ��龰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8�����ɷ�һ��19��Ů��ʱ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û�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п�ľ������Ǹ�Ů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ĸ��û���ٻ飬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ͬ�ӡ����Ů��16�꿪ʼ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ٵ�ԭ���ǻ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6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ٽ�300Ԫ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̥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Ϊ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źͶԸ��ԵĿ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Ȳ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ǡ����Ѵ�ͳ�ͽ��ɵĴ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���ɷö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ÿһ�βɷõ����룬���ٿ�ʼ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𣿡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о�η��û�п־塣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ӣ����Dz���Ϊ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Ҫ֪���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پ������ɷö���ɧ�š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ɧ�š��ij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Ů����̫û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Ǻ�ֱ�Ӻܡ��ᡯ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ҵľ����ܷḻ���ɷ�һ�θ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ץ���ֻ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dzԷ����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Ϻ��ķdz�Ư�����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Ů���ˣ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Ŀ�ľ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һ���߿�Ѱ���µġ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ٲɷ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ʲɷ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ƻ���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Ȼ��ڣ����ٶԼ��߶�Ȼ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һ���ð��̲���19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15�꿪ʼ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ٲɷ�ʱ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봫Ⱦ���ˡ�Ů��˵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ۣ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к�Ů���ڵð��̲���ʼ���ַŵ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ȫ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ҳ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Ҫ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ۿ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߸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ѣ���Ҫ֪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С��һЩ�ٶ��ް���֣�ֻ�ܸ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˺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걨��2002��10��22�գ�����ɳ�֣�ԭ�⣺����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ˡ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