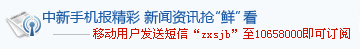≈∑—Ù”¶ˆ´µƒœ„∏€£∫∂‘Œ“¿¥Àµ°∞º“°±æÕ «“ª∂Œ¿˙ ∑
°°°°≈∑—Ù”¶ˆ´µƒœ„∏€ º“ «–ƒ÷–µƒ¿˙ ∑
°°°°≈∑—Ù”¶ˆ´ œ„∏€øÁΩÁ¥¥◊˜»À£¨”Œ◊þ¡Ω∞∂»˝µÿ£¨π§◊˜…ʺ∞…˺∆°¢–¥◊˜°¢ªÊª≠°¢≥ˆ∞ʵ»∂ý∏ˆ¡Ï”Ú£¨”√À˚◊‘º∫µƒª∞¿¥◊ÐΩ· «°∞ ∏÷æ◊ˆ∏ˆÃ∞–ƒµƒ£¨øϪӵƒ£¨»œ’ʵƒøÁ√Ωõº”Œ°±°£◊˜∆∑”–°∂Œ“µƒÃÏ°∑°¢°∂∞ƵΩÀ¿°∑µ»¬˛ª≠œµ¡–£¨ÕºŒƒ¥¥◊˜”–°∂“ª»’“ª»’°∑°¢°∂—∞≥£∑≈µ¥°∑°¢°∂¡Ω∏ˆ»À◊°°∑°¢°∂ªÿº“’Ê∫√°∑°¢°∂œ„∏€Œ∂µ¿°∑µ»°£
°°°°≈∑—Ù”¶ˆ´∂•◊≈“ªÕ∑±Í÷æ–‘µƒ¬ð–˝◊¥∞◊∑¢£¨Ã∏µΩø™–ƒ ± ÷ŒË◊„µ∏£¨œÒ∏ˆ¥Ûƒ–∫¢°£¥”¬˛ª≠°¢µÁî°¢“˚ ≥°¢¬√”ŒµΩº“攅˺∆£¨’‚ŒªøÁΩÁµƒ∂ý√ΩÃÂ¥¥◊˜»À£¨“ª÷±‘⁄∂Ø”√∏˜÷÷ ÷∂Œ√˪Ê◊‘º∫–ƒƒø÷–µƒœ„∏€°£ «µƒ£¨œ„∏€ «œ„∏€»Àµƒæ´…Òº“‘∞£¨œ„∏€»À–ƒ¿Ô∂º◊∞◊≈“ª±æªÚ∫ÒªÚ±°µƒº“ ∑°£
°°°°œ„∏€ ∞¸¿®œ„∏€µ∫°¢æ≈¡˙∞ε∫°¢–¬ΩÁµ»µÿ«¯£¨√ʪ˝‘º1104∆Ω∑Ωπ´¿Ô£¨»Àø⁄≥¨π˝700ÕÚ°£¥Û”Ï…ΩŒª”⁄œ„∏€Œ˜ƒœ√Ê£¨ «œ„∏€æ≥ƒ⁄◊Ó¥Ûµƒµ∫”Ï£¨√ʪ˝146.75∆Ω∑Ωπ´¿Ô£¨±»œ„∏€µ∫¥Û84%°£¥Û”Ï…Ω¥Û≤ø∑÷µÿ«¯ Ù”⁄¿Îµ∫«¯£¨◊Ó∏þ∑Â∑ÔªÀ…Ω∏þ934√◊£¨ÃÏÃ≥¥Û∑◊¯¬‰”⁄¥Û”Ï…Ω±¶¡´À¬£¨ «»´«Ú◊Ó¥Ûµƒ “Õ‚«ýÕ≠∑œÒ°£
°°°°¥”«∞ œ„∏€ «“ª∂Œº«“‰
°°°°∂‘Œ“¿¥Àµ£¨°∞º“°±æÕ «“ª∂Œ¿˙ ∑°£
°°°°Œ“…˙≥§‘⁄œ„∏€£¨µ±»ªø…“‘Àµ «µÿµ¿µƒœ„∏€»À°£µ´ «Œ“√«’‚–©»Àµƒ…œ“ª¥˙£¨Œ“√«µƒ∏∏ƒ∏£¨∂º «‘ÁƒÍ¥”ƒ⁄µÿ“∆æ”π˝¿¥µƒ°£À˚√«‘⁄ƒ«∏ˆ ±¥˙ø…ƒÐ“ÚŒ™÷÷÷÷’˛÷ŒªÚæ≠º√…œµƒ‘≠“Ú£¨±»»ÁÔƒ—¿¥œ„∏€£¨ªÚ’þπ˝¿¥◊ˆ…˙“‚£¨±æ¿¥√ª”–¥ÚÀ„‘⁄œ„∏€¡Ùœ¬¿¥°£
°°°°œ„∏€≤ª «∏∏±≤√«µƒº“°£”¢π˙÷≥√ÒÕ≥÷Œ ±¥˙£¨œ„∏€ «±ª∏Ó»√≥ˆ»•µƒ£¨œ„∏€»À”–∏ˆÀµ∑®Ω–°∞ΩË¿¥µƒø’º‰°¢ΩË¿¥µƒ ±º‰°±£¨ø’º‰∫Õ ±º‰∂º «∂Ñð∂¯≤ª»∑∂®µƒ£¨≤ª÷™Œ¥¿¥‘⁄∫Œ∑Ω°£Œ“µƒ∏∏ƒ∏º∏∫ı «°∞≤ª–°–ƒ°±¿¥µΩœ„∏€£¨æ≠π˝¡À…œ∏ˆ ¿ºÕ¡˘∆þ ƃͥ˙µƒæ≠º√∆∑…£¨À˚√«∏’∏’ø™ ºœý–≈£¨œ„∏€ «◊‘º∫µƒº“°£¬Ì…œµΩ¡À1967ƒÍ£¨ ÐµΩƒ⁄µÿ°∞ŒƒªØ¥Û∏Ô√¸°±µƒ”∞œÏ£¨œ„∏€“≤∑¢…˙¡À±©∂Ø£¨◊Û≈…◊þ…œΩ÷Õ∑∂‘øπ∏€”¢’˛∏Æ°£ƒ« ±∫ÚŒ“ªπ–°£¨¥Û‘º¡˘∆þÀÍ£¨º«“‰÷–µƒ∏–æıæÕ «°∞Õ‚Õ∑”–»»ƒ÷°±£¨ÀºŒ¨…œÀ∆∫ı“≤ «ΩÙ’≈∂¯–À∑еƒ£¨œÒ‘⁄ø¥œ∑°£
°°°°Œ“º“◊°‘⁄æ≈¡˙≥«¿Ô£¨1982ƒÍŒ“‘⁄æ≈¡˙—≠µ¿÷–—ß∂¡ÕÍ¥Û—ß‘§ø∆£¨»ª∫Û»•ƒÓœ„∏€¿Ìπ§—ß‘∫µƒ…˺∆œµ£¨æÕ’‚—˘¿Îø™º“ø™ º«®·„°£Àµ ««®·„£¨∆‰ µ“≤≤ªπ˝∞·º∏¥Œº“∂¯“—°£µΩƒø«∞Œ™÷πŒ“‘⁄œ„∏€“ªπ≤∞·π˝ŒÂ¥Œº“£¨¥”≥«¿Ô‘Ω¿¥‘ΩÕ˘Ωº«¯»•£¨¥”»»ƒ÷µƒ –æÆ£¨–° ±∫Ú Ïœ§µƒΩ÷«¯£¨‘Ω¿¥‘Ω¿Î»∫À˜æ”°£∆‰ µœ„∏€µƒ—ß–£¥Û∂º√ª”–◊°–£“ªÀµ£¨“ÚŒ™√ª”–∑øº‰∏¯—ß…˙√«◊°£¨À˘“‘∂ý ˝»À∂º «◊°‘⁄◊‘º“£¨µ´Œ“»¥“™∞·≥ˆ¿¥£¨∫Õ“ª∏ˆƒ–Õ¨—ß°∞ը攰±°™°™°™’‚∏ˆ¥ Àµ∆¿¥∫√–¶£¨µ± ±’ʵƒ”–¡ÌÕ‚µƒÕ¨—ߌ۪·Œ“∏˙À˚ «°∞ƒ«÷÷πÿœµ°±£¨“ÚŒ™∏’«…À˚µƒº“»À∞·◊þ¡À£¨Œ“æÕ◊°µΩÀ˚º“¿Ô»•°£Œ“√«∫Г™∫√£¨’ʵƒÀØ‘⁄Õ¨“ª’≈¥≤…œ£¨÷ª «√ª”–∑¢…˙ ≤√¥πÿœµ∂¯“—°£
°°°°∫Ð∫√Õʵƒ¥Û—ß ±π‚£¨Œ“◊°‘⁄Õ¨—ߺ“”–≤ªµΩ“ªƒÍµƒ ±º‰£¨ø™ º¬˝¬˝æıµ√–Ë“™◊‘º∫∂¿¡¢µƒø’º‰°£’‚—˘æÕ∞·µΩ“ª∏ˆ–¬µƒ∑ø◊”¿Ô◊‘º∫◊°£¨∑øº‰∫Ж°£¨≤ªπ˝ ƺ∏∆Ω£¨¿ÎŒ“º“≤ª‘∂°£∫п√µƒ∑øº‰£¨µ´ «∫Ðø™–ƒ°£”–∂ý…Ÿ»Àª·∞—◊‘º∫◊°π˝µƒÀ˘”–∑øº‰£¨∞¸¿®æ∆µÍ£¨∂º≈ƒœ¬’’∆¨¿¥£øŒ“æÕ—¯≥…¡À’‚—˘µƒœ∞πþ°£º¥±„ «¡Ÿ ±¬‰Ω≈µƒµÿ∑Ω£¨ƒ«“≤ «Œ“√«…˙ªÓπ˝µƒø’º‰£¨ «Œ“√«≈º»ªªÒµ√µƒº“°£”»∆‰œ÷‘⁄ ÷ª˙°¢œýª˙’‚√¥«·±„£¨Œ“ª·¡Ù“‚≈ƒœ¬√ø“ª’≈Œ“ÀØπ˝µƒ¥≤°£æ՜Җ°≈Û”—ª·”–√ŒœÎ£¨‘⁄ ˜…œΩ®‘Ï“ª◊˘ ˜Œð£¨œ÷¥˙∂º –¿Ôµƒ–°∫¢ø…ƒÐ≤ª‘Ÿ◊ˆ’‚—˘µƒ√Œ£¨µ´“¿»ªª·œ£Õ˚”–ƒ≥÷÷∂¿¡¢°¢ÀΩ√еƒø’º‰ Ù”⁄◊‘º∫°£
°°°°ªÿπÈ ∂ص¥÷–µƒæ´…Ò—∞’“
°°°°Œ“‘⁄¥Û—ß¿Ô◊ˆµƒ±œ“µ¬€ŒƒΩ–◊ˆ°∂œ„∏€º“æ”π€ƒÓ°∑£¨“ÚŒ™ «–¥≥ˆ¿¥“™Ωª∏¯¿œ ¶∆¿∑÷µƒ∂´Œ˜£¨À˘“‘∫лœ’Ê£¨ŒÞ¬€»Á∫Œ“™Ω≤≥ˆ“ª–©π€µ„°£Œ“µ± ±æÕ∑÷Œˆœ„∏€»À∂‘”⁄°∞º“°±µƒ»œ÷™£¨µ√≥ˆ“ª∏ˆ¥∞∏£∫‘⁄œ„∏€£¨°∞º“°±µƒπ€ƒÓ∆‰ µ «∆∆¡—µƒ°¢¿Î…¢µƒ°£
°°°°Œ™ ≤√¥’‚—˘Ω≤£ø‘⁄∞À ƃͥ˙Œ“∂¡ ȵƒ ±∫Ú£¨µÀ–°∆Ω“—æ≠æˆ∂®“™ ’ªÿœ„∏€£¨’‚ «≤ªø…ƒÊ◊™µƒ¥Û ∆£¨À˘”–‘⁄œ„∏€…˙ªÓµƒ»À£¨µΩ’‚∏ˆ ±º‰∂º“™÷ÿ–¬Àºøº£¨◊‘º∫µƒº“‘⁄ƒƒ¿Ô£ø∫Ð∂ý»ÀœÎµΩ“™“∆√Ò£¨»•º”ƒ√¥ÛªÚ’þ∞ƒ÷Þ£¨Œ“º“»À“≤”–π˝’‚—˘µƒøº¬«°£æ≠¿˙¡˘∆þ ƃͥ˙π˝¿¥µƒ»À£¨–ƒ÷–…‘…‘∞≤∂®£¨◊º±∏‘⁄œ„∏€‘˙∏˘œ¬¿¥£¨’‚ ±∫Ú“ÚŒ™“™°∞ªÿπÈ°±£¨À˚√«”÷‘⁄∑◊∑◊¿Îø™°£∫√œÒ¬˝¬˝ƒ˝æ€∆¿¥µƒœ„∏€£¨Õª»ª”÷…¢µÙ¡À°£
°°°°’‚ ±∫Ú∂ص¥µƒ∏–æı£¨≤≈’Ê’˝≥ª˜Œ“µƒ–ƒ¡È°£…̱þ∫Ð∂ý≈Û”—“∆√Ò£¨Œ“∞÷¬Ë∏˙Œ“√√√√“≤≥ˆ»•¡À£¨µΩº”ƒ√¥Û°£»ª∫ÛŒ“∏˙Œ“µÐµÐ“≤“ª∆π˝»•µΩƒ«±þø¥ø¥£¨µ´’ʵƒ÷ª «ø¥ø¥£¨π˝“ª∏ˆ¿Ò∞ðæÕ”÷≈Ъÿœ„∏€°£¿œ µΩ≤Œ“≤ªœ∞πþº”ƒ√¥Ûµƒ…˙ªÓ£¨œƒÃϪπ∫√£¨µΩ¥¶∂º «¬Ã…´£¨µ´Œ“√«»´º“π˝»•µƒ ±∫Ú «∂¨ÃÏ£¨ µ‘⁄ Ð≤ª¡Àƒ«¿Ôµƒ∫Æ¿‰°£µ±Œ“¿Îø™œ„∏€£¨’‚ ±∫Ú≤≈ƒÓ∆œ„∏€µƒ∫√°£”– ≤√¥ «œ„∏€¡ÓŒ“∏Ó…·≤ªœ¬µƒ£ø…˙ªÓª∑æ≥°¢≥‘µƒ°¢∫»µƒ£¨’‚–© «±»Ωœ±Ì√Ê…œµƒ∂´Œ˜£¨Œ“æıµ√◊Ó∑≈≤ªœ¬µƒ£¨ «‘⁄œ„∏€¿€ª˝≥ˆ¿¥µƒ“ª÷÷ªÏ¥Óµƒæ´…Ò°£¥”∞À ƃͥ˙ø™ º£¨À‰»ªŒ“√«“ª÷±ªπ‘⁄∏€”¢’˛∏ÆÕ≥÷Œœ¬√Ê£¨µ´ «œ„∏€»Àª·∏–æıµΩ«±‘⁄µƒ÷∏“˝£¨¿¥◊‘ƒ⁄µÿ’˛∏Ƶƒƒ≥÷÷∂Ø◊˜ªÚ’þè∂»£¨“ª÷±µΩæ≈∆þªÿπÈÀ„ «’˝ ΩΩ”πÐπ˝¿¥°£‘⁄’‚∏ˆ“‚“Â…œ£¨»Áπ˚“™Àµœ„∏€æ´…Ò£¨ªÚ’þœ„∏€◊˜Œ™Œ“µƒæ´…Òº“‘∞µƒ±æ÷ £¨Œ“æıµ√æÕ «ƒ«÷÷”–µ„ÕÁ∆§°¢”–µ„∏„π÷°¢”–µ„∫√ÕÊ∫Õ°∞≤ª“ª—˘°±µƒ∏ˆ–‘£¨º“≥§≤ª“ª∂®œ≤ª∂£¨µ´ «–°∫¢◊”◊‘º∫∫Ðø™–ƒ°£
°°°°Œ“∏∏ƒ∏‘⁄º”ƒ√¥Û◊°¡À»˝ƒÍ∂ý“≤ªÿ¿¥¡À£¨÷ª”–√√√√∫Õ√√∑Ú“ª÷±¡Ù‘⁄ƒ«±þ£¨Œ“∫ÕŒ“µÐ‘⁄œ„∏€”–π§◊˜°£Œ“¿Îø™—ß–£◊ˆ¡À“ª–©…˺∆∑Ω√ʵƒπ§◊˜£¨æıµ√ªπ≤ªπª£¨æÕ”÷≈Ъÿ—ß–£∂¡µ⁄∂˛∏ˆ—ߌª°£1987ƒÍ±œ“µµƒ ±∫Ú£¨∏∏ƒ∏≤ªœ˛µ√¥”ƒƒ¿Ô’“¿¥“ª± «Æ£¨ÃÊŒ“¥˚øÓ¬Ú¡Àµ⁄“ª∏ˆ∑ø◊”°£œ„∏€±»Ωœ°∞¿˜∫¶°±µƒº“≥§ª·’‚—˘£¨‘⁄ƒ„ªπƒÍ«·µƒ ±∫Ú£¨À˚√«‘∏“‚∏¯ƒ„µ⁄“ª± «Æ£¨“ÚŒ™ƒ„ø™ ºπ§◊˜¡À£¨ø…“‘ø™ ºπ©∑ø◊”°£»√Œ“¬˙◊„”–◊‘º∫°∞ ˜Œð°±µƒ√ŒœÎ£¨æÕ¥”ƒ«∏ˆ ±∫Úø™ º°£
°°°°¿Îµ∫ æý¿Î÷–µƒœ„∏€Œ∂µ¿
°°°°1988ƒÍŒ“ø™ º‘⁄œ„∏€…ÓµµÁî◊ˆ ¬£¨“≤»•Ã®Õµ»µÿµΩ¥¶≈У¨µΩ1990ƒÍ¥”îÕªÿœ„∏€“‘∫Û£¨Œ“æÕ∞—º“∞·µ√”÷‘∂¡À“ª–©£¨µΩ¥Û”Ï…Ω£¨“≤æÕ «¿Îµ∫°£¿Îµ∫ «æ≈¡˙∞ε∫∫Õœ„∏€µ∫÷ÆÕ‚µƒ260∂ý∏ˆ–°µ∫£¨¥Û”Ï…Ω°¢≥§÷Þµ∫°¢ƒœ—æµ∫ «√ʪ˝±»Ωœ¥Ûµƒº∏∏ˆ¿Îµ∫°£‘⁄¥Û”Ï…Ω◊°µΩœ÷‘⁄øÏ“™∂˛ ƃ͡À£¨Œ“◊°µƒ…Á«¯¿Ô÷˜“™æ”√Ò «Õ‚π˙»À£¨À˘“‘Œ“∏˙≈Û”—ø™ÕÊ–¶ÀµŒ““—æ≠“∆√Ò¡À°™°™“∆√ÒµΩ¿œÕ‚±»÷–π˙»À∏¸∂ýµƒ…Á«¯£¨“∆√ÒµΩœ„∏€µƒ¿Îµ∫°£
°°°°◊°‘⁄¿Îµ∫£¨ª·≤ªª·∏–æı°∞œ„∏€Œ∂µ¿°±∏¸‘∂¡À“ª–©£ø∆‰ µŒ“æıµ√∫Ð∫√ÕÊ£¨“ÚŒ™Œ“Õ¶∞Æ◊¯¥¨£¨√øÃÏ◊¯¥¨Ω¯≥«£¨‘Ÿ¥”≥«¿ÔÕ∑◊¯¥¨ªÿº“£¨Œ“æıµ√’‚ «“ª∏ˆ∫Ð∫√µƒπ˝≥𣑯æ≠‘⁄“ª∆™Œƒ’¬¿ÔÕ∑Œ“–¥π˝£¨ÀµŒ“’Ê’˝æıµ√Ω≈ç µµÿµƒ ±º‰£¨ «¥”’‚¿Ôø™ º°£“ÚŒ™¬˝¬˝‘⁄“ª∏ˆ∏°∂صƒ◊¥Ã¨œ¬£¨Ω¯»ÎµΩ“ª∏ˆ“™π§◊˜ƒ±…˙µƒ¥Û≥«£¨∫√œÒº§¡“‘À∂Ø÷Æ«∞µƒ≈Ø…Ì°£µΩ¡Àœ¬∞ýµƒ ±∫Ú£¨”÷ «’‚—˘µƒ“ªÀ“¥¨£¨‘ÿ◊≈Œ“¬˝¬˝ªÿº“£¨ª˘±æ…œ“ª…œ¥¨Œ“æÕæıµ√“—æ≠ªÿº“¡À£¨“ÚŒ™‘⁄¥¨…œø…“‘ÀØæı£¨ø…“‘ø¥ È£¨«¯±÷ª «√ª”–Õ—œ¬ø„◊”∂¯“—°£
°°°°ƒ«∏ˆ¥¨∫Ð…Ò∆Ê£¨∞Ζ° ±“ª∞ý£¨»´ÃÏ24–° ±∂º”–°£◊ÓΩ¸º∏ƒÍ”÷ø™Õ®¡ÀÀ̵¿£¨ø…“‘◊¯∞Õ øΩ¯≥ˆ¿Îµ∫£¨Œ“ªπ «∏¸œ≤ª∂◊¯¥¨°£◊°‘⁄¿Îµ∫µƒ…˙ªÓ «„´“‚µƒ£¨»Áπ˚Àµœ„∏€ «Œ“º“£¨∫√œÒÕª»ª∑¢æıº“√≈ø⁄‘≠¿¥”–’‚√¥∆Ø¡¡µƒ∑Áæ∞£¨∫Õ∏¸º”◊‘”…µƒ…˙ªÓ∑Ω Ω°£µ∫…œ≤ªø…“‘ø™≥µ£¨À˘“‘ƒÐ𪱣≥÷∫Ж¬œ µƒø’∆¯£¨Œ“√øÃÏ‘Á…œŒÂµ„∂ý∆¿¥£¨“ÚŒ™◊°‘⁄…Ω…œ±»Ωœ∏þµƒµÿ∑Ω£¨“™◊þ¬∑∆¬Î∞Î∏ˆ–° ±œ¬¿¥£¨≥ˆ“ª…Ì∫π°£’‚∂Œ ±º‰¿Ôø¥◊≈ô—Ù¬˝¬˝…˝∆¿¥£¨”–µ„œÒ¿œƒÍ»Àµƒ–ƒÃ¨°£
°°°°»À’ʵƒ¿œ¡Àµƒª∞£¨–ƒÃ¨ª·∏¸∆´œÚª≥æ…£¨“≤–̪·∏¸œÎƒÓ◊°‘⁄≥«¿Ô√Ê“ªº“»Àµƒ∏–æı°£¿œ µÀµŒ“»¥≤ª‘ı√¥ª≥æ…£¨“≤≤ª¡µº“£¨ø…ƒÐŒ“ª·‘ΩªÓ‘ΩœÒ–°∫¢°£æ”◊°ª∑æ≥’ʵƒø…“‘”∞œÏ»Àµƒ–ƒÃ¨£¨Œ““ª—˘¿ÌΩ‚‘⁄ƒ÷ –«¯æ”◊°µƒ°¢…Ì¥¶…Óµ…Áª·÷–µƒœ„∏€»À£¨±œæπŒ““≤ «¥”ƒ«∏ˆª∑æ≥¿Ôπ˝¿¥µƒ°£∏’≤≈÷µΩœ„∏€æ´…Ò£¨∂‘£¨œ„∏€æ´…ÒæÕ «ø™∑≈°¢∞¸»ð£¨Œ“∑≈≤ªœ¬µƒæÕ «œ„∏€Ãÿ ‚µƒ¿˙ ∑£¨—¯≥…’‚√¥“ª÷÷’‰πÛµƒ∑’Œß°£œ„∏€»À∞Æ¥Ú∆¥£¨Œ“—™“∫¿Ô“≤”–’‚—˘µƒª˘“Ú£¨±»Ωœ«⁄∑Ð∫Õπ§◊˜øÒ£¨µ´ «Œ“∏¸‘∏“‚÷≥´°∞≤ª“ª—˘°±µƒ…˙ªÓ∑Ω Ω°£»Àº“œ≤ª∂…œ∞ý√ª”– ≤√¥≤ª∫√£¨ø…≤ª“ª∂®√ø∏ˆ»À∂º“™πÊπÊæÿæÿ…œ∞ý£¨”¶∏√”–¡ÌÕ‚µƒ—°‘Ò£¨»√–°≈Û”—√«æıµ√OK£¨‘≠¿¥”––©π÷  Âø…“‘’‚—˘≤ª…œ∞ýªÓ◊≈£¨∫√œÒªÓµ√ªπ¬˘ø™–ƒ°™°™°™’‚ «Œ“’˝‘⁄¿ÌΩ‚µƒ£¨À˘ŒΩ…Áª·‘»Œ°£
°°°°°∞º“°± ≥ŒÔ¿Ô”–Œ“√«∂‘œ„∏€µƒ∏–«È
°°°°°∞º“°± «“ª∏ˆ¡˜∂صƒ∏≈ƒÓ£¨’‚≤¢≤ª–¬œ °£π˙Õ‚∫БÁæÕ”––©»Àœ≤ª∂∞—º“∞≤‘⁄¥Û≈Ò≥µ…œ£¨œÒº™≤∑»¸»Àƒ«—˘¡˜¿À°£Œ“√«–ƒ¿Ôµƒº“£¨“≤–Ì «“ª≤ø≥µ°¢“ª’≈¥≤£¨“≤ø…“‘ «“ª∏ˆ–°ƒ÷÷”°¢“ª±≠≤Ë…ı÷¡“ª∏ˆ∑Ω±„√Ê°£º“£¨◊Ъ·”–≤ªÕ¨µƒœÎœÛ°£
°°°°’‚—˘»À–ƒ∂ص¥µƒœ„∏€£¨∫√œÒ◊Б⁄“ªª·∂˘∑≈¥Û£¨“ªª·∂˘”÷Àı–°°£µΩ¡Àæ≈∆þ÷Æ∫Û£¨¥Ûº“æıµ√∫√œÒªπOK—Ω£¨æÕ”÷∑◊∑◊¥”Õ‚√ʪÿ¿¥°£◊˜Œ™œ„∏€»À£¨∂‘°∞º“°±µƒ’‚—˘“ª÷÷…Ó≤„µƒø¥∑®£¨ πµ√Œ“ø™ º”–“‚ ∂µÿ»•◊ˆπ˝»•’‚ ƺ∏ƒÍµƒπ§◊˜°£
°°°°±»»Á£¨‘⁄1997ƒÍ◊Û”“Œ“ø™ º∏¯“ª±æ‘”÷æ◊ˆπÿ”⁄°∞º“°±µƒ◊®¿∏£¨◊ˆ¡À≤Ó≤ª∂ý»˝ƒÍ£¨æÕ «∞—°∞º“°±≤ø™¿¥£¨Ã∏¬€¿Ô√ÊÀ˘”–¡„¡„ÀÈÀȵƒ∂´Œ˜°£“≤–Ì”√“ª∆™Œƒ’¬¿¥Ã∏¥∞◊”£¨‘Ÿ–¥“ª∆™¿¥Ã∏◊¿◊”°£Œ“’“…̱þ¡ΩŒª∫Г™∫√µƒ≈Û”—¿¥µ±ƒ–≈ƃ£Ãÿ£¨∞Á—ð“ª∏ˆº“Õ•÷–µƒ¡Ω∏ˆƒÍ«·»À£¨≈ƒ…„∫Ð∂ýπÿ”⁄º“攜∏Ω⁄µƒ’’∆¨£¨’‚—˘≥ˆ¿¥“ª±æ ÈæÕ «°∂¡Ω∏ˆ»À◊°°∑°£‘⁄’‚∏ˆ◊®¿∏¿Ô£¨Œ“∞—◊‘º∫πÿ”⁄°∞º“°±µƒæ≠—È£¨“‘º∞“ª–©≈Û”—µƒæ≠—È£¨∂º∑≈Ω¯“ª∏ˆæþõƒº“攪∑æ≥÷–¿¥°£
°°°°¡ÌÕ‚“ªº˛ ¬æÕ «Œ“»•≤…∑√¡Àº∏ ÆŒª∏˜∏ˆ¡Ï”Úµƒ¥¥◊˜»À£¨’˚¿Ìº«¬ºÀ˚√«µƒº“°£Õ∆ø™À˚√«µƒº“√≈◊þΩ¯»•£¨Œ“÷™µ¿£¨’‚∏ˆº“ «’‚Œª¥¥◊˜»À◊Óæ´≤ µƒ◊˜∆∑°£ŒÞ¬€À˚√«◊ˆ“Ù¿÷“≤∫√£¨ªÊª≠“≤∫√£¨ªÚ’þΩà Ȗ¥◊÷£¨∆‰ µ∂ºÕ∂»Î∫Ð∂ý ±º‰∏˙æ´¡¶‘⁄°∞º“°±µƒΩ®ππ…œ√Ê°£√ø∏ˆº“∂º”–𠬣¨‘ı√¥Àµ“≤Àµ≤ªÕÍ°£±»»Á◊˜º““∂‚˘¿º£¨ «Œ“‘⁄îÕ“ª∏ˆ∫Г™∫√µƒ≈Û”—£¨Œ“≈ƒ…„À˝µƒ≥¯∑ø£¨”–“ª√Ê≤£¡ßπÒ◊”∑≈◊≈–Ì∂ý≤˱≠£¨æðÀµÀ˝√øÃÏ∂º”√≤ªÕ¨µƒ≤˱≠∫»≤Ë°£’‚–©…˙ªÓ¿ÔÕ∑µƒ–°∂Ø◊˜£¨±»Àø¥∆¿¥π÷π÷µƒ£¨∆‰ µ∂º∑«≥£’Ê µ°£œ„∏€”–∏ˆ∑˛◊∞…˺∆ ¶µÀ¥Ô÷«£¨Œ“»•À˚‘⁄‘™¿ µƒ¿œº“£¨ƒ« «’Ê’˝µƒ¿œ’¨£¨ø…ƒÐ”–Àƒ∞ŸƒÍ¡À°£À˚¥Û∏≈ «œ÷‘⁄œ„∏€ªπ◊°‘⁄¿œ∑ø◊”¿Ôµƒ…Ÿ ˝»À÷Æ“ª£¨√øÃÏ π”√ƒ«–©π≈¿œµƒƒæ÷ ◊¿“Œ£¨¥•√˛µΩæ≠µ‰µƒœ„∏€°™°™’‚±æ È «°∂ªÿº“’Ê∫√°∑°£
°°°°¡ÌÕ‚£¨Œ““≤¬˝¬˝∞—¥¥◊˜µƒΩ𵄣¨◊™“∆µΩ∏˙“˚ ≥ŒƒªØœýπÿµƒ ¬ŒÔ…œ»•£¨ ◊“™µƒ»ŒŒÒ «’˚¿Ìœ„∏€µƒ ≥ŒÔ£¨“≤æÕ «°∂œ„∏€Œ∂µ¿°∑°£’‚ «Œ“∂‘œ„∏€’‚∏ˆ°∞º“°±£¨À˘◊ˆµƒ÷ÿ–¬ºÏ ”°£Œ“∑¢æıœ„∏€»À»Áπ˚»•Õ‚√Ê◊þ¡À“ª»¶£¨ªÿµΩœ„∏€Œ“√«µ⁄“ª∏ˆŒ ÂæÕª· «°∞ƒ„‘⁄Õ‚√Ê≥‘¡À ≤√¥°±£¨±»À÷™µ¿Œ“ «œ„∏€»À£¨“≤≥£≥£ª·Œ πÿ”⁄“˚ ≥µƒŒ °£∆‰ µ’‚–©Œ µƒ≤ª « ≥ŒÔ£¨∂¯ «∂‘°∞º“°±µƒ“ª÷÷∂®“°£“ªÕΑ∆ÕÃ√Ê£¨“ª∏ˆƒÃ≤Ë£¨æÕµ»”⁄Œ“√«’‚–©»À∂‘”⁄œ„∏€µƒ∏–«È°£ ≥ŒÔ”–’‚√¥…Ò∆Ê°¢Œ¢√Óµƒ∫¨“£¨¥Ûº““≤∏√”–≤ªÕ¨µƒ∞Ê±æ¿¥Ω‚∂¡°£±»∑ΩÀµœ∫Ω»£¨Œ“—–æø÷Æ∫Û≤≈÷™µ¿£¨¥´Õ≥µƒœ∫Ω»‘≠¿¥”¶∏√”–11Ω⁄°£ªπ”–øæ»È÷Ì£¨Œ“µΩ“ªŒª ¶∏µµƒº“¿Ôø¥À˚ø™ ºø棨µΩ»È÷Ì≥ˆ¬Ø£¨“ª∏ˆ∂ý–° ±£¨À˚√ª”–∑¢≥ˆ“ªµ„…˘“Ù£¨ÕÍ»´◊®◊¢‘⁄‘ı—˘øæ∫√ƒ«Õ∑»È÷Ì°£¡¨Œ“’‚—˘µƒ≈‘π€’þ£¨∂ºª·ÃÊÀ˚Ωæ∞¡£∫Œ“√«∂º «œ„∏€»À£¨ƒ„ø¥Œ“µƒº“»À∂‘¥˝π§◊˜∂ý√¥◊®◊¢°£
°°°° ±º‰
°°°°º“ «–ƒ÷ÆÀ˘∞≤
°°°°‘¯æ≠»√Œ“∏–µΩ∂ص¥≤ª∞≤µƒœ„∏€£¨‘⁄1997ƒÍ÷Æ∫Û÷’”⁄∞≤∂®œ¬¿¥°£≤ª÷™µ¿œ„∏€»À «∑Ò”–’‚∞„ÀÞ√¸£¨√øπ˝ ƺ∏∂˛ ƃͣ¨æÕª·÷ÿ–¬µ˜’˚◊‘º∫∂‘”⁄°∞º“°±µƒ»œ÷™°£µΩ¡À—«÷ÞΩ»⁄∑Á±©µƒ ±∫Ú£¨¥Ûº“∫ЫÂ≥˛£¨’‚≤ªπ˝ «æ≠º√∑Ω√ʵƒƒ≥÷÷≤®∂Ø£¨≤ªø…±Ð√‚£¨“≤–Ìªπª·”–œ¬“ª≤®£¨’˚∏ˆ…Áª·“—æ≠¬˘≥… Ï£¨ø…“‘»•‘§∑¿∫Õµ÷”˘’‚÷÷≥ª˜¡À°£À˘“‘¥Ûº“–ƒ¿Ôªπ∫Ð∞≤∂®£¨∏¸∫Œøˆ“˛“˛‘º‘º÷™µ¿£¨÷–—Ϊ·∞Ôœ„∏€∞⁄∆Ωµƒ°™°™œ„∏€’‚∏ˆº“£¨”–¡Àƒ∏«◊°£
°°°° ±¥˙◊Д–∑Á¿À£¨Œ“√«œÎµΩŒ¥¿¥◊Д–ô∂ýµƒ≤ª»∑∂®£¨Ã´∂ýµƒ≤ª∞≤Œ»°£µ´ «”–º“æÕ∫√£¨ƒƒ≈¬÷ª «“ª∏ˆ–°–°µƒ∑øº‰£¨Œ“√«∂º‘∏“‚ªÿº“°£
°°°°Œ“µ±»ª“≤»»∞Ƭ√––£¨–Ì∂ýæ∆µÍµƒπ„∏ʪ·Àµ°∞make yourself at home°±£¨±ˆ÷¡»Áπȵƒ“‚Àº£¨Œ“æÕÕ®π˝¬√––¿¥øº÷§£¨æøæπ”–√ª”–’‚÷÷ø…ƒÐ°£”–¥Œ»•∞տµ∫£¨◊°‘⁄“ª∏ˆœ„∏€≈Û”—‘⁄ƒ«±þµƒ∂»ºŸŒð¿Ô£¨ƒ«Œð◊”æ”»ª‘⁄µæÃÔ¿Ô±þ°£Œ“º∏∫ı√ª”–œÎœÛπ˝£¨’‚±≤◊””–ª˙ª·‘⁄≈©ÃÔ¿Ô◊°…œƒ«√¥º∏ÃÏ£¨Œ“‘∏≤ª‘∏“‚∞—’‚¿Ôµ±≥…Œ“Œ¥¿¥µƒº“ƒÿ£ø’‚ «“ª∏ˆ∫Ð∫√µƒ∑¥Àºª˙ª·£¨æÕµ± «‘⁄º“¿ÔÕ∑◊ˆ“ª≥°√Œ∫√¡À°£Œ“Õ‚π´ «”°ƒ·ª™«»£¨À˘“‘Œ“µ»”⁄ «≤ª–°–ƒ◊þªÿ¿œº“£¨∑¢œ÷Œ“µƒº“∆‰ µ”–ƒ≥∏ˆ≤ø∑÷‘⁄ƒœ—Û’‚∏ˆµÿ∑Ω°£Œ™ ≤√¥Àµº“æÕ «¿˙ ∑£ø∫Ð∂ý ±∫Úƒ„ª·≈º»ª÷ÿ–¬¥≥Ω¯ƒ„◊‘º∫º“µƒ¿˙ ∑÷–°£∫Ð∆Ê√Ó£¨º“Õ‚”–º“£¨∆‰ µ’‚∏ˆº“¥”¿¥∂º¥Ê‘⁄£¨÷ª «ƒ„√ª”–‘ø≥◊¥Úø™ƒ«…»√≈∂¯“—°£
°°°°Œ“æ≠≥£Ω®“È≈Û”—£¨»Áπ˚µΩœ„∏€µƒª∞£¨ŒÞ¬€‘ı—˘“≤∏√»•◊¯“ª¥Œª˙≥°øÏœþ°™°™ƒ« «÷ª”√≤ªµΩ∞Î∏ˆ–° ±£¨æÕƒÐ∫√∫√»œ ∂œ„∏€µƒ∑Ω Ω°£ƒ„¥”≈©¥Â≥ˆ∑¢£¨æ≠π˝“ª∏ˆπ§“µ∑¢’π≥ı∆⁄µƒ≥« –£¨Ω¯»Î√Ò攣¨Ω¯»Î∏þ¬•¥Ûœ√£¨Ω¯»ÎΩ»⁄∫ՅÓµµƒ÷––ƒ£¨»ª∫ÛµΩ¥Ô∫£∏€°™°™œÒ∂ت≠∆¨“ª—˘∆Ê√Ó°£Õ®π˝ø’º‰µƒ±‰ªØ£¨∑¬∑“≤ø¥µΩ¡À ±º‰µƒ±‰ªØ£¨œ„∏€æÕ «¥”“ª∏ˆ–°”Ê¥Â∑¢’πµΩΩÒÃϵƒ°£
°°°°≥˝¥À÷ÆÕ‚£¨»Áπ˚“™Àµœ„∏€’‚∏ˆ°∞º“°±µƒµÿ±Í£¨Œ“æıµ√ô∆Ω…Ω∂•ªπ «“™»•ø¥£¨ƒ„ø…“‘æ°¡øÕ¸º«÷бþµƒΩ®÷˛£¨÷ª¥”“ª∏ˆ÷∆∏þµ„»•∏© ”œ„∏€£¨∫Ð√¿°£
°°°°»ª∫Û£¨æÕ «¿Îµ∫°£Œ“æıµ√œ„∏€“Àæ”÷Æ¥¶‘⁄”⁄’‚¿Ô£¨¥” –«¯µΩΩº«¯◊Ðπ≤“≤≤ªπ˝∞Î∏ˆ–° ±£¨œ„∏€∫Ðø…∞Æ£¨¥Û–°’˝∫œ °£
°°°°¥Û‘º∂˛ ƺ∏ƒÍ«∞£¨Œ“‘¯æ≠ΩË”√”¢π˙»Àµƒ“ª∏ˆÀµ∑®£¨»•«ÎΩÃ∂≠«≈œ»…˙£¨À˚ ««∞±≤∑≠“Î√˚º“°£Œ“Àµ”–’‚—˘“ªæ‰ª∞£∫°∞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.°±«ÎŒ ∂≠œ»…˙∏√‘ı√¥∑≠“΃ÿ£øÀ˚æÕ∏¯¡ÀŒ““ª∏ˆ∑«≥£µ‰—≈µƒÀµ∑®£∫°∞º“ «–ƒ÷ÆÀ˘∞≤°£°±Œ“∞—’‚扪∞”√‘⁄°∂ªÿº“’Ê∫√°∑µƒø™∆™£¨æÕ «“ÚŒ™ÀµµΩµ◊£¨πÿ”⁄œ„∏€’‚∏ˆº“£¨ªπ «“™Ã∏µΩ»À£¨Ã∏µΩ»À–ƒ£¨Ã∏µΩœ„∏€»À «≤ª «’ʵƒø…“‘”–“ª÷÷∞≤–ƒµƒ∏–æı°£’‚÷÷∏–æı“≤–Ì∫Ð∂Ñ𣨵´ƒ≥“ª∏ˆ ±øÄæıµ√OK£¨ƒ«æÕ∫√¡À°£
°°°°º«’þ Œ‰‘∆‰þ
 ≤Œ”Ϊ•∂Ø(0) ≤Œ”Ϊ•∂Ø(0) |
°æ±ýº≠:’≈÷–Ω≠°ø |
-
----- ŒƒªØ–¬Œ≈æ´—° -----
- °§¿•«˙°∂ƒµµ§Õ§°∑¡¡œý¬Ì∂˙À˚ ∂´Œ˜∑Ωπ≈¿œŒƒªØº§«È≈ˆ◊≤
- °§ÃΩ∑√°∂¬Íƒ…Àπ°∑∑«ŒÔ÷ ŒƒªØ“≈≤˙¥´≥–»À ÿª§√Ò◊Â÷«ª€
- °§“‘¥´≤•…Áª·—ß ”Ω«ÃΩÀ˜£∫–¬÷–π˙≈Æ–‘–ŒœÛ±‰«®
- °§∆Ø—Ûπ˝∫£µƒ°∞—Û√¿∫ÔÕı°±£∫∞—æ©æÁ≥™∏¯ ¿ΩÁÃ˝
- °§À´”Ôœý…˘”Î÷⁄≤ªÕ¨£∫µ±œý…˘”ˆ…œ°∞Õ·π˚» °±
- °§Ωı¿°¢∑œµ°¢πŸ–˚...Õ¯¬Á¡˜––”Ô≥…ŒƒªØ∑˚∫≈
- °§π π¨Õ∆≥ˆ°∞≥ı—©°±µ˜¡œπÞ Õ¯”—£∫≥¯∑ø÷±Ω”…˝º∂”˘…≈∑ø
- °§µ⁄ Æ»˝ΩϪ∆µ€ŒƒªØπ˙º ¬€Ã≥£∫—ß’þ“‘ ´∏ËΩ≤ ˆº“π˙«Èª≥
- °§≤ª…·¬√∞ƒ¥Û–Ð√®ªÿπ˙£°∞ƒ¥Û¿˚—«Ω´◊‚∆⁄—”≥§5ƒÍ
- °§¿˙ ±3ƒÍøÁ‘Ω33π˙ ∫…¿ºƒ–◊”ÕÍ≥…µÁ∂Ø≥µª∑«Ú÷Ƭ√
- °§∑¬Þ¿Ô¥Ô÷ðπ˙º“≤∂ªÒæÞÚ˛ ≥§∂»≥¨5√◊Ã⁄”–73ø≈µ∞
- °§∏£‘≠∞Æ∆Ω∞≤≤˙œ¬∂˛Ã• ¿œπ´Ω≠∫ÍΩÐœ≤…π“ªº“Àƒø⁄(Õº)
- °§º”ƒ√¥Û“ª≤һƓڪ·ª≠ª≠◊þ∫Ï ª≠◊˜“— €≥ˆ”‚231∑˘
- °§º””Õ«πŒ¥ ’Àæª˙ºð≥µ∂¯»• º””Õ’æ…œ—ð晪ÍÀ≤º‰
- °§∆Ø—Ûπ˝∫£µƒ°∞—Û√¿∫ÔÕı°±£∫∞—æ©æÁ≥™∏¯ ¿ΩÁÃ˝
- °§Ω∫∂´¡“ ø¡Í‘∞»Îø⁄¿¨ª¯±Èµÿ°¢Õ£≥µ¬“ ’∑—£øπŸ∑Ωªÿ”¶
- °§Ω·ªÈ¬ Ωµ¿ÎªÈ¬ …˝ «∂¿¡¢“‚ ∂·»∆ªπ «∑øº€Ã´πÛ£ø
- °§Õ¯∫σ͖Ω∞ŸÕÚ£ø –≥°µ˜≤È£∫Ωˆ20%µƒÕ∑≤øÕ¯∫Ï‘⁄◊¨«Æ
- «∞π˙º ∞¬ŒØª·÷˜œØ»¯¬Ì¿º∆Ê ≈ ¿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
- Õº£∫∞¬ŒØª·…œµƒ»¯¬Ì¿º∆Ê
- ”Ò ˜µÿ’‘÷«¯“ª“π∑Á—© øπ’滑÷±∂º”ºËƒ—(...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(2)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(3)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(4)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(5)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(6)
- Õº£∫∏þæ´º‚æØ”√≤˙∆∑∫Õºº ı¡¡œýæ©≥«(7)
- »’œµ∆˚≥µ«∞∆þ∏ˆ‘¬‘⁄ª™œ˙¡øΩ¸200ÕÚ¡æ ƒÊ...
- °æÕºøØ°ø√˙º«¿˙ ∑ ƒ™Õ¸¿œ±¯
- °∞9.3°±¥Û‘ƒ±¯»´¡˜≥Ã∆ÿπ‚ °∞Ω⁄ƒøµ•°±…œ...
- π˙º ”Õº€–◊√Õ∑¥µØ π˙ƒ⁄∆˚≤Ò”Õº€∏Ò¡˘¡¨µ¯
- 30À̓–◊”¬˙¡≥÷ÂŒ∆»Á80ÀÍ¿œÕ∑ “¯––»°«Æ...
- ∞ŸÀÍøπ»’¿œ±¯Ω؃Ð
- ∫”ƒœ500ƒ∂◊غ⁄ ’ªÒ‘⁄º¥±ª«ø≤˘ »Œ–‘»«√Ò‘π
- °∞◊ӱ؅À◊˜Œƒ°±∑¢≤º’þ“—ªÿº“ ≥∆÷ª «≈‰∫œµ˜...
- ÷–π˙≥µ∆Û±»—«µœ¥øµÁ∂Ø¥Û∞Õ¡¡œý∞ÕŒ˜ •±£¬Þ≥µ’π
- °∞œ÷≥°÷∏»œ°±±‰°∞”ŒΩ÷ æ÷⁄°± œ”∑∏»®¿˚“™≤ª...
Copyright ©1999-2025 chinanews.com. All Rights Reserv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