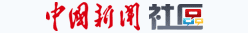(…ý√ų£ļŅĮ”√°∂÷–Ļķ–¬őŇ÷‹ŅĮ°∑łŚľĢőŮĺ≠ ť√ś ŕ»®)
°°°°“Ńőńňľ“Ľ“Ļ÷ģľš√Ż”Ģ…®Ķō£¨Ī≥…Ō∆≠◊”°Ę–Żīęľ“°Ęļ…ņľĶń°įņÔ∑“ňĻňĢ∂Ż°ĪĶ»őŘ√Ż°£ňŻ»Ōő™…„÷∆◊ť≥…‘Ī”–“‚∂‘ňŻ“Ģ¬ųŃňŃ÷ĪŽ ¬ľĢ£¨∂‘ňŻ√«īů∑Ę∆Ę∆Ý£ļń„÷™Ķņő“√«’‚–©÷–Ļķ»ňĶńŇů”—‘ŕĻķÕ‚”–∂ŗń—¬ū
°°°°ĪĺŅĮľ«’Ŗ/—Ó√Ű
°°°°1972ńÍ3‘¬£¨÷–Ļķ£¨ĪĪ∑ĹĶńīļŐž≥Ŕ≥ŔőīĻť°£ ņĹÁ÷™√ŻľÕ¬ľ∆¨Ķľ—›”»ņÔňĻ°§“Ńőńňľ£¨īÝ◊ŇŃĹ…Ūń•∆∆Ķńőų◊įļÕ…„”į◊įĪłņīĶĹĪĪĺ©°£”ŽňŻÕ¨––Ķń£¨ĽĻ”–ňŻĶń∑®ĻķŇģ”—°Ę“≤ «ļŌ◊ųĽÔįťĶń¬ÍňĻŃ’°§¬řņŲĶ§°£
°°°°’‚őĽĪĽ≥∆◊ų°įľÕ¬ľ∆¨÷ģłł°ĪĶńļ…ņľ»ň£¨ «”¶÷‹∂ųņī÷ģ—Ż∂ÝņīĶń£¨◊ľĪłŇń…„“Ľ≤Ņ∑ī”≥őńłÔĶńľÕ¬ľ∆¨°£
°°°°74ňÍĶń“Ńőńňľ”Ž÷–Ļ≤“Ľ÷ĪĪ£≥÷◊ŇŃľļ√ĶńĹĽ«ť°£‘Á‘ŕ1938ńÍ£¨ňŻņī÷–ĻķŇń…„∑ī”≥÷–Ļķ»ň√ŮŅĻ’ĹĶńľÕ¬ľ∆¨°∂ňńÕÚÕÚ»ň√Ů°∑ Ī£¨ĺÕĹŠ ∂Ńň÷‹∂ųņī°£ņŽŅ™÷–Ļķ«į£¨ňŻ√ō√‹Ĺę“ĽŐ®…„”įĽķļÕŃĹ«ß≥ŖĶńĹļ∆¨»√»ňňÕ÷Ń—”į≤£¨÷–Ļ≤ŃžĶľ»ň≤ŇĶ√“‘ŃŰŌ¬‘ŕ—”į≤Ķń‘Á∆ŕ”įŌŮ°£
°°°°īň Ī£¨ńŠŅňň…◊‹Õ≥∑√Ľ™ł’Ļż£¨∑‚Ī’“—ĺ√Ķń÷–Ļķ«ń»ĽŌÚőų∑Ĺ…ž≥ŲŃňťŌť≠÷¶°£
°°°°ľłļű”Ž“ŃőńňľÕ¨ Ī£¨“‚īůņŻĶľ—›į≤∂ęńŠį¬ńŠ“≤”¶—ŻņīĶĹ÷–ĻķŇń…„ľÕ¬ľ∆¨°£ňŻĶńőų∑Ĺ ”Ĺ«Ķń◊ų∆∑°∂÷–Ļķ°∑÷Ľ”√22ŐžĺÕÕÍ≥…Ńň°£”į∆¨1973ńÍ‘ŕĻķÕ‚…Ō”≥ļů£¨‘ŕ÷–Ļķ‘‚”ŲŃň√ÕŃ“ŇķŇ–°£
°°°°°įĶĪ Ī—ß–£°ĘĽķĻō°Ę≤Ņ∂”∂ľńŕ≤Ņ◊ť÷ĮĻŘŅī°∂÷–Ļķ°∑°£°Ī“ŃőńňľĶń∑≠“Ž¬ĹňŐļÕňĶ£¨°įń«∂ő Īľšĺ≠≥£”–Ňů”—īÚĶÁĽįņīőŅő £¨ňŻ√«“‘ő™ő“ «į≤∂ęńŠį¬ńŠĶń∑≠“Ž°£°Ī
°°°°1972ńÍ£¨ĺ≠”…ĶĪ ĪĶń÷–—Ž–¬őŇĶÁ”į÷∆∆¨≥ß≥ß≥§∂°ŠĹÕ∆ľŲ£¨‘ŕ»ęĻķłĺŃ™Ļķľ ≤ŅĻ§◊ų(ĶĪ ĪĪĽĹŤĶųĶĹŃň∂‘Õ‚”—–≠)Ķń¬ĹňŐļÕĶ£»őŃň“ŃőńňľĶń∑≠“Ž°£īňļů£¨“Ńőńňľņī÷–Ļķ∆ŕľš£¨¬ĹňŐļÕ∂ľłķňś◊ů”“£¨“Ľ÷ĪĶĹ1988ńÍňŻ◊Óļů“Ľīőņī÷–Ļķ°£
°°°°°į“Ńőńňľ∂‘∑≠“Ž“™«ůļ‹łŖ£¨≥żŃň◊Ų”Ô—‘…ŌĶńĻĶÕ®£¨ňŻĽĻ“™«ů∑≠“Ž «ňŻ‘ŕ÷–ĻķŇń…„Ļż≥Ő÷–Ķń°ģ∂ķńŅļŪ…ŗ°Į°£°Ī¬ĹňŐļÕłśňŖ°∂÷–Ļķ–¬őŇ÷‹ŅĮ°∑°£ńÍ”‚įň—ģĶń¬ĹňŐļÕ“—ī”»ęĻķłĺŃ™ņŽ–›∂ŗńÍ£¨ĪĪīů∑®”ÔŌĶĪŌ“ĶĶńňż£¨…Ū…ŌĪ£ŃŰ◊Ň–¬÷–ĻķĶŕ“Ľīķ÷™ ∂Ňģ–‘ĶńļŘľ££ļ»»«ť÷ ∆”°Ęņ÷”ŕĻĶÕ®°£ňżļ‹‘ł“‚”Ž»ňŐł∆ūņŌŇů”—“Ńőńňľ°£
°°°°“ŃőńňľĶńľÕ¬ľ∆¨ņķ Ī6ńÍ≤ŇÕÍ≥…°£”į∆¨‘≠ņīĶń√Ż◊÷Ĺ–°∂Ķŕ∂Ģīő≥§’ų°∑£¨ļů»°√ę‘ů∂ęĶń“Ľ∆™őń’¬Ķń√Ż◊÷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ő™∆¨√Ż°£
°°°°“Ńőńňľ ÷Õ∑≥£īÝ◊Ň“ĽĪĺőųįŗ—ņőńĶń°∂√ę‘ů∂ę—°ľĮ°∑°£∆š÷–£¨°∂‘ŕ—”į≤őń“’◊ýŐłĽŠ…ŌĶńĹ≤Ľį°∑“Ľőń£¨ňŻ”√ļžņ∂…ęĪ Ľģ¬ķŃňł‹ł‹°£ňŻ∑«≥£Ōŗ–Ň√ę‘ů∂ę£¨Ōŗ–Ň°įőńłÔ «“Ľ≥°ī•ľį»ň√«ŃťĽÍĶńłÔ√Ł°Ī°£ňŻŌŽŌÚőų∑ĹĻŘ÷ŕ≥ Ō÷őńłÔłÝ»ň√Ů…ķĽÓīÝņīĶń–¬√ś√≤£¨°į“‘’ż ”Őż°Ī°£
°°°°Ņ¶ ≤ō¨√ő
°°°°1972ńÍ4‘¬£¨“ŃőńňľĶń…„÷∆◊ť ◊Ō»įīľ∆ĽģņīĶĹŃň…Ĺőųīů’Į°£
°°°°≥żŃň∑≠“Ž¬ĹňŐļÕ£¨“ŃőńňľĶń…„÷∆◊ťĽĻįŁņ®Ńž∂”“∂ Ĺīļ£¨“‘ľį“Ľ√ŻłĪĶľ—›°ĘŃĹ√Ż…„”į ¶°ĘŃĹ√ŻĶ∆Ļ‚ ¶ļÕ“ĽłŲįžĻę “––’ĢÕ‚Ń™»ň‘Ī°£Ňń…„Ķń»’≥Őį≤ŇŇ”…∂‘Õ‚”—–≠łļ‘ū£¨÷–—Ž–¬őŇľÕ¬ľĶÁ”į÷∆∆¨≥ßŐŠĻ©ľľ ű÷ß≥÷°£
°°°°’ŻłŲ…„÷∆◊ť∂ľ÷™Ķņ£¨÷‹◊‹ņŪĹĽīķŃň£ļ’‚ «“ŃőńňľĶńĶÁ”į£¨“™įī’’“ŃőńňľĶń“‚Õľ»•Ňń…„°£÷‹∂ųņīłśňŖ“Ńőńňľ£ļ”√≤Ľ◊Ň’ŕ’ŕ—ŕ—ŕ£¨÷–Ļķ «łŲ«ÓĻķ£¨ «Ķ໿ ņĹÁĶńĻķľ“£¨Ķō”ÚŃ…ņę“≤łńĪš≤ĽŃň’‚łŲ ¬ Ķ°£”√≤Ľ◊ŇŇń“Ľ≤Ņ∑Ř őŐę∆ĹĶń∆¨◊”£¨÷–Ļķ « ≤√ī—ýĺÕ‘ű√īŇń£¨≤Ľ“™į—÷–ĻķŇń≥…“Ľ∂š√ĶĻŚĽ®°£
°°°°ĶęĶŕ∂ĢŐž“Ľ‘Á£¨“ŃőńňľĺÕ∑ĘŌ÷£¨īů’ĮŃžĶľ»ň≥¬”ņĻů“ĽłŲ»ňŅł◊Ň≥ķÕ∑‘ŕ…Ĺ…ŌĽ”ļĻ»Á”Í°£ňŻĶĪľīҧÕ∑ĺÕ◊Ŗ°£
°°°°°į“ŃőńňľĶńĺĶÕ∑ī”≤Ľ∂‘◊ľŃžĶľ£¨÷Ľ∂‘◊ľ»ň√Ů°£°Ī¬ĹňŐļÕňĶ°£°įňŻ“Ľ÷Ī«ŅĶų’‚≤Ņ”į∆¨°ģ»√»ň√ŮňĶĽį°Į°£°Ī
°°°°“Ńőńňľ‘ŕīů’Į≤›≤›ŇńŃňľłŐžĺÕņŽŅ™Ńň£¨◊Ó÷’“≤√Ľ‘ŕľÕ¬ľ∆¨÷–≤…”√īů’ĮĶńňō≤ń°£
°°°°»ÁĻŻ’‚–©“ŃőńňľĽĻń‹»Ő ‹ĶńĽį£¨ń«√ī‘ŕŅ¶ ≤Ķńĺ≠ņķ£¨‘ÚĪĽňŻ≥∆ő™°įŅ¶ ≤ō¨√ő°Ī£¨“≤÷ĪĹ”Ķľ÷¬Ńň◊„◊„ŃĹłŲįŽ‘¬ĶńŇń…„÷–∂ŌļÕ…„÷∆◊ť»ň‘ĪĶų’Ż°£
°°°°‘ŕŅ¶ ≤£¨“ŃőńňľŐŠ≥ŲĶĹ√Ņ÷‹őŚĶńįÕ‘ķ(◊‘”… –≥°)»•Ňń…„°£Ķō∑Ĺ’Ģłģ◊®√ŇłÝĺ”√Ů∑ĘŃňļž¬ŐĽ∆»ż…ę…ŌĹ÷∆Ī£¨”√≤ĽÕ¨Ķń—’…ęĻś∂®Ńň…ŌĹ÷Ķń Īľš°ĘĶōĶ„°Ę◊Ň◊į£¨…ű÷ŃĪŪ«ť°£ĺ”√Ů√«∑Ģ◊įŌ ŃŃ°Ę—ů“Á◊Ň–¶Ń≥£¨‘ŕĺĶÕ∑«į’Ļ ĺ–“ł£°£∂Ý‘ŕ◊‘”… –≥°£¨…Ő∆∑Ń’ņҬķńŅ£¨ĻňŅÕ√«ŇŇ∂”Ļļ¬Ú£¨‘ŕĻŮŐ®ŃŪ“ĽĪŖ‘ŔÕňĶŰ°£
°°°°“Ńőńňľļ‹…ķ∆Ý£¨ĺŲ∂®ŃĘŅŐÕ£Ľķ°£
°°°°°įňŻ»Ōő™Ķō∑Ĺ’Ģłģő•Ī≥Ńň÷‹◊‹ņŪĶń÷ł ĺ£¨≤Ľł√»√ňŻ”√…„”įĽķ»•∆Ř∆≠ ņĹÁ»ň√Ů°£°Ī¬ĹňŐļÕňĶ°£“ŃőńňľĽĻ÷ł‘ū…„÷∆◊ťĶńĻ§◊ų»ň‘Ī£¨√Ľ”–”ŽĶō∑Ĺ’ĢłģĹÝ––”––ßĶńĻĶÕ®°£
°°°°…„÷∆◊ť≥∑ĽōĪĪĺ©°£“ŃőńňľŇ≠∆Ý≥Ś≥ŚĶōłÝ Ī»őÕ‚ĹĽ≤ŅĻňő Ńő≥–÷ĺ–ī–Ň£¨Ō£ÕŻń‹ŇšĪł“ĽłŲ∂ģĶÁ”įļÕņķ ∑°Ę≤Ę«“ń‹ňĶ∑ĢĶō∑Ĺ’Ģłģ∑Ģī”÷–—ŽĶń»ňņīłļ‘ū…„÷∆◊ť°£
°°°°…„÷∆◊ťĶńŃž∂”“∂ Ĺīļ «∂‘Õ‚”—–≠Ķńł…≤Ņ£¨ňż‘ÝĽō“š£ļ°į“Ńőńňľ’Ģ÷ő–Šĺűļ‹Ńť√Ű£¨ňŻń‹Ņī≥Ųņī°≠°≠ĶĪ ĪőńĽĮīůłÔ√Ł£¨∑«≥£«Ó£¨≤ľ÷√Ķńń«–©∂ęőų¬ų≤Ľ◊°ňŻĶń°£ő“√«…„÷∆◊ťĺÕ◊ů”“ő™ń—Ńň£¨”÷“™–Żīę’‚–©∂ęőų£¨–ńņÔ”÷≤ĽÕ®£¨“Ńőńňľ”÷≤ĽĹ” ‹£¨ňý“‘Ļ§◊ųļ‹ņßń—°≠°≠ń« ĪļÚő“łķ¬ĹňŐļÕ◊°‘ŕĪĪĺ©∑ĻĶÍ£¨ő“ľ«Ķ√ŃųĻż—ŘņŠ£¨ĺűĶ√ļ‹őĮ«Ł°£°Ī
°°°°ŃĹłŲ‘¬ļů£¨Ńő≥–÷ĺŇ…ŃňĻķőŮ‘ļÕ‚ ¬įžĻę “÷ų»ő«ģņÓ» ņīłļ‘ū…„÷∆◊ťĶńĻ§◊ų£¨“∂ Ĺīļ–≠÷ķňŻĻ§◊ų°£°į«ģņÓ» ī” ¬Õ‚ ¬Ļ§◊ųļ‹∂ŗńÍ£¨ňŻ◊Ų ¬≥Ńő»ŃťĽÓ£¨–ń“≤Ōł°£°Ī¬ĹňŐļÕňĶ£¨°į“∂ Ĺīļňš»Ľ ‹Ńň–©őĮ«Ł£¨Ķę“ĽĶ„“≤√ĽĪß‘Ļ£¨łķ∆Ĺ≥£“Ľ—ý»Ō’śłļ‘ūĶōĻ§◊ų°£°Ī
°°°°ĪĽ—°‘ŮĶń’ś Ķ
°°°°ī”1973ńÍ1‘¬÷Ń4‘¬£¨“Ńőńňľ“Ľ÷Ī‘ŕ…Ōļ£Ķ໿“©ĶÍ£¨ĻŘ≤žĶÍ‘Ī√«Ķń…ķĽÓ£¨”ŽňŻ√«ĹĽŇů”—°£
°°°°ŇģĶÍ‘ĪįŁļ≠£¨1970ńÍīķń©‘Ý ‹—Ż≤őľ”…Ōļ£ĶÁ”įĺ÷◊ť÷ĮĶń“Ľīőńŕ≤ŅĻŘ”įĽÓ∂Į£¨Ņī’‚≤ŅľÕ¬ľ∆¨°£
°°°°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»ę≥§12–° Ī£¨”…12≤Ņłų◊‘∂ņŃĘĶń”į∆¨◊ť≥…°£°∂…Ōļ£Ķ໿“Ĺ“©…ŐĶÍ°∑ «∆š÷–“Ľ≤Ņ°£
°°°°°įļ‹’ś Ķ£¨ĶĪ ĪĺÕ «ń«łŲ—ý◊”°£°ĪįŁļ≠∂‘°∂÷–Ļķ–¬őŇ÷‹ŅĮ°∑ňĶ£¨°įňŻ√« «∂‘Õ‚”—–≠Ĺť…‹ņīĶń£¨ňý“‘ő“√«“≤√Ľ”–ŅĻĺ‹£¨ Īľš≥§Ńň£¨ŅīĶĹĺĶÕ∑“≤≤ĽĹŰ’Ň°£°Ī
°°°°”į∆¨÷–£¨ĶÍ‘Ī√«ĶńĪŪ«ť∂Į◊ų’ś Ķ◊‘»Ľ£¨’‚“Úīň≥…ő™“ŃőńňľļÕ¬ÍňĻŃ’ļůņī◊ÓŌ≤Ľ∂Ķń≤Ņ∑÷÷ģ“Ľ°£
°°°°∆š÷–“Ľ◊ťĺĶÕ∑ «‘ŕįŁļ≠ľ“Ňń…„Ķń°£°į“ĽĽōľ“£¨–°įŁÕý…≥∑Ę…Ō“ĽŐ…£¨Ī’◊Ň—ŘŐż ’“ŰĽķ°£»ĽļůĺĶÕ∑ĺÕ◊™ĶĹŃň‘ļ◊”ņÔ£¨–°įŁįģ»ň‘ŕŅ‘ŖÍŅ‘ŖÍĶōŌī“¬∑Ģ°£°Ī¬ĹňŐļÕĽō“š°£
°°°°ĽōĪŲĻ›ļů£¨…„÷∆◊ťļÕ¬ÍňĻŃ’‘ŕ—ŰŐ®…Ō∑Ę…ķŃň’ý¬Ř°£¬ĹňŐļÕĶ»÷–∑Ĺ»ň‘Ī»Ōő™£¨’‚∂őňō≤ń≤Ľļ√°£÷–ĻķłĺŇģňš»ĽĹ‚∑ŇŃň£¨Ķę“≤≤Ľń‹—Ļ∆»ń–»ň£¨’‚ŐŚŌ÷Ńňń–Ňģ≤Ľ∆ĹĶ»°£
°°°°ĶęįŁļ≠÷ŃĹŮ≤Ľ»Ōő™’‚ «ń–Ňģ≤Ľ∆ĹĶ»°£°į’‚÷Ľ «∑÷Ļ§≤Ľ“Ľ—ý°£…Ōļ£Ķńľ“Õ•∂ľ’‚—ý°£“Ľ÷ĪĶĹŌ÷‘ŕő“ľ“∂ľ’‚—ý°£°ĪňżňĶ°£
°°°°“ŃőńňľľŠ≥÷‘ŕ”į∆¨÷–≤…”√Ńň’‚“Ľ∂ő°£”į∆¨ļůņī‘ŕįÕņŤĻę”≥ Ī£¨“ŃőńňľļÕ¬ÍňĻŃ’ ō‘ŕ”į‘ļ√ŇŅŕŐżĻŘ÷ŕĶń∑īņ°°£ĶĪňŻ√«ŐżľŻ”–∑®ĻķŇģ◊”ł–Őĺ÷–ĻķłĺŇģĶńĹ‚∑Ň£¨∂ݬّĻń–”—‘ŕľ“≤Ľ◊Ųľ“őŮ Ī£¨ņ÷Ńň°£
°°°°Õ¨—ýłÝ»ň“‘’ś Ķł–Ķń£¨ĽĻ”–”į∆¨°∂«ÚĶńĻ ¬°∑°£’‚≤Ņ∆¨◊”Ĺ≤ ŲŃň∑Ę…ķ‘ŕĪĪĺ©Ķŕ31÷–—ßĶńĻ ¬°£‘Á…Ō7Ķ„‘Á◊‘ŌįŅ™ ľ÷ģļů£¨ņŌ ¶ĹŻ÷Ļ—ß…ķ‘ŔŐŖ«Ú£¨Ķę“ĽłŲ—ß…ķ»Ő≤Ľ◊°∑…∆ū“ĽĹŇ£¨«Úī”ņŌ ¶ĶńÕ∑∂•∑…Ļż°£ņŌ ¶ļ‹…ķ∆Ý£¨Ňķ∆ņŃň—ß…ķ£¨√Ľ ’Ńň◊„«Ú°£
°°°°”į∆¨’Ļ ĺŃň ¶…ķ÷ģľšĶń“Ľ≥°√Ů÷ųĪÁ¬Ř£ļ—ß…ķő™ ≤√ī”–ŐŖń«“ĽĹŇ«ÚĶń≥Ś∂Į£ŅņŌ ¶ «∑Ů–°Ő‚īů◊ų£¨√Ľ ¬’“≤Á£Ņ
°°°°◊ÓļůŐŖ«ÚĶń—ß…ķ∑ī °£¨◊‘ľļ∂‘ņŌ ¶Ķń≥…ľŻ‘Ķ”ŕ”–“ĽīőņŌ ¶∂‘ňŻĶń°įőřņŪ°Ī÷ł‘ū£ĽņŌ ¶“≤»Ōő™◊‘ľļ◊ÓŅ™ ľĺÕį——ß…ķĽģ◊ųīŪőůĶń“Ľ∑Ĺ£¨√Ľ”–≥š∑÷Ņľ¬«—ß…ķĶńŌŽ∑®°£
°°°°ňę∑Ĺ∆ĹĶ»°ĘņŪ–‘ĶńŐ¨∂»£¨»√»ň≤ĽĹŻĽ≥“…Ļ ¬Ķń’ś Ķ–‘°£
°°°°2003ńÍ£¨ĪĪĺ© ¶∑∂īů—ßĹŐ ŕ’ŇÕ¨ĶņĹę‘≠įŗ—ß…ķ«ŽĽōĹŐ “£¨Ľō“šĶĪ ĪĶń«ťŅŲ°£ĶĪńÍĶń—ß…ķ“—»ňĶĹ÷–ńÍ£¨ĶęňŻ√«÷ŃĹŮ»‘»Ľ»Ōő™£¨“ŃőńňľŇń…„Ķń£¨∂ľļ‹’ś Ķ°£
°°°°Ķę“Ńőńňľ◊‘ľļ“≤«Ś≥Ģ£¨ļ‹∂ŗ ĪļÚ£¨ňŻ≤ĽĶ√≤Ľ√ś∂‘ĺ≠Ļż—°‘ŮĶń°į’ś Ķ°Ī°£
°°°°°į‘ŕőųį≤Ňń…„ Ī£¨ő“√«ŅīľŻĶĪ Ī”–Ňķ∂∑Ķń”ő––≥ĶņīŃň£¨∆Ż≥ĶňĺĽķŃĘŅŐĻ’ĶĹŃŪ“ĽŐűĹ÷…Ō°£°Ī¬ĹňŐļÕĽō“š°£
°°°°¬ĹňŐļÕ‘Ýĺ≠»√¬ÍňĻŃ’į—“™ŌÚŇń…„∂‘ŌůŐŠĶńő Ő‚Ō»łÝňż£¨“‘√‚ĶĪ≥°∑≠“ŽĶ√≤Ľ◊ľ»∑£¨Ķę¬ÍňĻŃ’Ľōīūňż£ļ°į≤Ľ––£¨»ŰłÝń„Ńň£¨ń„ĽŠÕĶÕĶłśňŖňŻ√«£¨ňŻ√«ĽŠ”–◊ľĪłĶōĽōīū£¨ń«≤Ľ «ő“√«ŌŽ“™Ķń°£°Ī
°°°°61Őű–řłń“‚ľŻ
°°°°1975ńÍ£¨“ŃőńňľļÕ¬ÍňĻŃ’īÝ◊Ň“—ÕÍ≥…Ķń7≤Ņ”į∆¨ĽōĶĹĪĪĺ©°£
°°°°°į”–“ĽŐžÕŪ…Ō£¨“ŃőńňľļÕ¬ÍňĻŃ’‘ŕĪĪĺ©∑ĻĶÍ≥ŲŌĮ“Ľ≥°īū–Ľĺ∆ĽŠ£¨ÕĽ»Ľ÷–Õĺ’Ňīļ«ŇÕ®÷™…ů∆¨°£»ęŐŚ…„÷∆◊ť≥…‘ĪľĪľĪ√¶√¶łŌĶĹ»ň√ŮīůĽŠŐ√»ż¬•Ķń–°ņŮŐ√°£°Ī¬ĹňŐļÕĽō“š°£
°°°°–°ņŮŐ√◊ÝĶ√¬ķ¬ķĶĪĶĪĶń°£≤őľ”…ů∆¨Ķń≥ż Ī»őłĪ◊‹ņŪ’Ňīļ«ŇÕ‚£¨ĽĻ”–őńĽĮ≤Ņ≤Ņ≥§”༊”ĺ°ĘłĪ≤Ņ≥§Ńű«žŐńĶ»»ň°£¬ĹňŐļÕľ«Ķ√£¨Ńű«žŐń∑Ę—‘ļ‹∂ŗ°£
°°°°”į∆¨÷–”–“Ľ∂ő£¨“Ńőńňľ‘ŕīů”śĶļłķī¨Ō¬ļ££¨≤…∑√ī¨≥§£ļ°įń„ņŪĹ‚őńłÔ¬ū£Ņ°Īī¨≥§»Á ĶĽōīū£ļ°į≤ĽņŪĹ‚°£°Ī“Ńőńňľ»Ōő™’‚ŐŚŌ÷Ńň»ň√Ů∂‘”ŕőńłÔĶńňľŅľ£¨Ķę…ů∆¨’Ŗ»īłÝ”ŤŃň—Ōņų÷ł‘ū£ļ°į»ęĻķ»ň√Ů∂ľņŪĹ‚őńłÔ£¨ő™ ≤√īňŻ≤ĽņŪĹ‚£Ņ°Ī“™«ů…廕’‚“Ľ∂ő°£
°°°°≥żīň÷ģÕ‚£¨–řłń“‚ľŻĽĻįŁņ®£ļ≤Ľ“™į—◊ųő™ňŐłŤĶń°∂∂ę∑Ĺļž°∑”Ž…Ōļ£¬š”Í°Ę»ļ÷ŕīÚ…°ĶńĽ≠√śŃ¨Ĺ”£ĽĻę‘įņÔÕ∆∂ýÕĮ≥ĶĶń–°ĹŇŇģ»ňĶńĺĶÕ∑”¶ľŰĶŰ£¨ĽÚľ”“ĽĺšĹ‚ňĶ£¨ňĶ√ų’‚ «ĺ…÷–Ļķ“ŇŃŰŌ¬ņīĶń£¨÷Ľ”–60ňÍ“‘…ŌĶńłĺŇģ≤Ň”––°ĹŇ£Ľ»’≥Ų«įĹ≠…Ō«Ś≥ŅĶńĺĶÕ∑∑ĘĽ“£¨ĽŠ»√»ňŃ™ŌŽĶĹőŘ»ĺ£¨÷Ó»Áīňņŗ£¨Ļ≤61Őű°£
°°°°∂‘”ŕ’‚–©∆ň√ś∂ÝņīĶńŇķ∆ņļÕ÷ł‘ū£¨łŲ–‘Ō √ųĶń¬ÍňĻŃ’—ŕ ő≤Ľ◊°“ĽŃ≥„≥Ň≠£¨“Ńőńňľ»ī“‘≥Ńń¨◊ųīū°£
°°°°“Ńőńňľń‹ł–ĺűĶĹ£¨ňš»ĽĹ≠«ŗ≤Ľ‘ŕ…ů∆¨Ō÷≥°£¨Ķę «ňżĶń“ű”įőřī¶≤Ľ‘ŕ°£
°°°°1971ńÍ£¨“ŃőńňľĶĹ÷–Ļķ∑√ő Ī£¨Ĺ≠«ŗ‘Ý»żīőľŻňŻ£¨ňńīőŇ„ňŻŅī—ýįŚŌ∑£¨įĶ ĺňŻő™ňżŇń“Ľ≤ŅłŲ»ňľÕ¬ľ∆¨£¨“Ńőńňľ≤Ľ÷√Ņ…∑Ů£Ľ1974ńÍ£¨Ĺ≠«ŗ”÷ ŕ“‚ňŻĻęŅ™∑ĘĪŪőń’¬£¨ŇķŇ–į≤∂ęńŠį¬ńŠ£¨ĪĽňŻĺ‹ĺÝŃň£ļ°įő“√«Õ¨—ýł„ĶÁ”į£¨łų”–łųĶń“’ ű ÷∑®£¨≤ĽĪ„”ŕŇķŇ–°£°Ī
°°°°…ů∆¨ĹŠ Ýļů£¨…„÷∆◊ťĽōĶĹĺ”◊°ĶńĪĪĺ©∑ĻĶÍ°£°į“Ľ¬∑…Ō∂ľļ‹≥Ńń¨°£°Ī¬ĹňŐļÕĽō“š£¨°įĶĹ∑ĻĶÍļů£¨ĺÕłų◊‘Ľō∑Ņ°£ő“√«“≤≤Ľł“ňĶ ≤√ī°£°Ī
°°°°īň ĪĶń÷–Ļķ£¨’żī¶”ŕ’Ģĺ÷ĺřĪšĶń«įŌ¶°£≤°ī≤…ŌĶń÷‹∂ųņīÕ–»ňłÝ“ŃőńňľīÝĽį£ļį—’‚–©”į∆¨īÝ…Ō£¨ń‹ĺ°Ņž◊ŖĺÕĺ°Ņž◊Ŗ£¨‘› Ī≤Ľ“™‘ŔĽō÷–ĻķņīŃň°£
°°°°ĪĽ°įĻ ŌÁ°Ī(“Ńőńňľ ”÷–Ļķő™Ķŕ∂Ģ◊śĻķ)ĺ‹÷ģ√ŇÕ‚£¨∂‘“ŃőńňľņīňĶ£¨‘Á“—≤Ľ «Ķŕ“Ľīő°£
°°°°ńÍ«Š Ī£¨“Ńőńňľ“Úő™∑ī∂‘◊‘ľļĶń◊śĻķļ…ņľ«÷¬‘”°ńŠ£¨ĪĽļ…ņľ’Ģłģ«ż÷ū≥Ųĺ≥£¨Ń¨ńł«◊»• ņ“≤√Ľń‹Ľōľ“ľŻ…Ō◊Óļů“Ľ√ś°£ļůņī“Ńőńňľ“Ľ÷ĪŃųÕŲŇ∑÷ř£¨÷ß≥÷ň’Ń™ļÕ∆šňŻ…ÁĽŠ÷ų“ŚĻķľ“Ķńőř≤ķĹ◊ľ∂∂∑’ý£¨ļÕ ņĹÁłųĻķ ‹—Ļ∆»’ŖĶń∂∑’ý°£ņš’Ĺ Ī£¨“Ńőńňľ“‚ ∂ĶĹň’Ń™ńŕ≤ŅĻŔŃŇ÷ų“Ś◊Ő≥§£¨÷–Ļķ≥…ő™ňŻĻ≤≤ķ÷ų“ŚņŪŌŽĶń◊Óļů∆‹ŌĘĶō°£īňļůňŻĶń√Ż◊÷ĪĽī”ň’Ń™–¬≥ŲįśĶńīůįŔŅ∆»ę ť÷–…ĺ≥ż°£
°°°°1975ńÍ9‘¬£¨–ń«ťĺŕ…•Ķń“ŃőńňľļÕ¬ÍňĻŃ’◊ľĪłĽōĻķ°£…„÷∆◊ťĶń»ęŐŚ≥…‘Ī«įņīĽķ≥°ŌŗňÕ°£“Ńőńňľ‘ŕĽō“š¬ľ÷––īĶņ£ļ°įő““Ľ…ķ÷–ī”őīľŻĻż»Áīň∂Į»ňĶńłśĪū≥°√ś°≠°≠ňŻ√«ĺŘľĮ‘ŕŌŌŐ›Ō¬£¨”√ňęĪŘĹŰĹŰĶō”ĶĪßő“√«£¨ļÕő“√«łśĪū°£īů∂ŗ ż»ň¬šŌ¬—ŘņŠ£¨ő“√«“≤őř∑®Ņō÷∆◊‘ľļ°£īůľ“∂ľ«Ś≥Ģ£¨ňŻ√«Ĺę‘Ŕ∂»√śŃŔīů”Ł£¨ő“√«‘Ŕ“≤≤Ľń‹ŌŗľŻŃň°≠°≠°Ī
°°°°ĶęňŻŌŽŌů÷–Ķń»ęŐŚŌ¬”ŁĶńĪĮ◊≥≤Ę√Ľ”–≥ŲŌ÷°£°įļůņī∆š Ķ∂‘ő“√«“≤√Ľ ≤√ī”įŌž°£“ĽńÍļůőńłÔĺÕĹŠ ÝŃň°£°Ī¬ĹňŐļÕňĶ°£
°°°° ß“Ķ ģńÍ
°°°°1976ńÍ3‘¬£¨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‘ŕįÕņŤĻę”≥£¨≥÷–ÝįŽńÍ£¨÷ģļů”į∆¨‘ŕ∂ŗĻķ…Ō”≥ĽÚ≤•≥Ų°£őų∑Ĺ»Áīň∆ņľŘ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£ļ°į“ŃőńňľįÔ÷ķő“√«Õ¨÷–Ļķ»ňĻ≤Õ¨…ķĽÓŃň“Ľ∂ő Īľš°£°Ī
°°°°1976ńÍ «∂ŗ ¬Ķń“ĽńÍ°£‘ŕőų∑Ĺ∑◊∑◊≤¬≤‚ Ī£¨“ŃőńňľĻęŅ™‘ŕĶÁŐ®–Ż≥∆£¨°į÷–Ļķ’Ģĺ÷ő»∂®°Ī£¨÷–Ļ≤ļÕ÷–Ļķ’Ģłģ√Ľ”–≥ŲŌ÷»őļőő Ő‚°£ňŻĶń—‘¬Ř“Ú∆š”Ž÷‹∂ųņīĶńňĹĹĽ∂ÝĪł ‹÷űńŅ°£
°°°°»Ľ∂ÝĹŲľłłŲ‘¬ļů£¨°įňń»ňįÔ°ĪĪĽ≤∂°£
°°°°“Ńőńňľ“Ľ“Ļ÷ģľš√Ż”Ģ…®Ķō£¨Ī≥…Ō“ĽŃ¨īģĶńőŘ√Ż£ļ∆≠◊”°Ę–Żīęľ“°Ę÷–Ļķ∑Ť◊”°Ę√§ńŅĶńĻ≤≤ķ÷ų“Ś’Ŗ°Ęőř»ň–‘ŐŚ÷∆Ķń–Żīęľ“°Ęļ…ņľĶńņÔ∑“ňĻňĢ∂Ż(ń…ī‚ĶÁ”į÷∆◊ų’Ŗ)°≠°≠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“≤ĪĽ»Ōő™ «“Ńőńňľ”Ž÷–Ļķ’ĢłģĻ≤ńĪĶńĹŠĻŻ£¨ «ő™őńłÔÕŅ÷¨ń®∑Ř°Ę∆Ř∆≠őų∑ĹĻŘ÷ŕĶń£¨‘‚ĶĹ“Ľ÷¬Ķ÷÷∆°£
°°°°1977ńÍ1‘¬£¨“ŃőńňľīÝ◊Ň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Ķń12≤Ņ”į∆¨‘ŔīőņīĶĹ÷–Ļķ°£‘ŕ…Ōļ£∑ĻĶÍ£¨ňŻ∂‘«įņīŅīÕŻňŻĶń…„÷∆◊ť≥…‘Īīů∑Ę∆Ę∆Ý£¨Ļ÷ňŻ√«√Ľ”–Ĺę°įŃ÷ĪŽ ¬ľĢ°ĪłśňŖňŻ°£¬ĹňŐļÕňĶ£ļ°įňŻĶĪ ĪňĶŃň“Ľĺš£ļń„÷™Ķņő“√«’‚–©÷–Ļķ»ňĶńŇů”—‘ŕĻķÕ‚”–∂ŗń—¬ū£Ņ°Ī
°°°°∂‘īň£¨¬ĹňŐļÕňĶ£¨ő“√«ĶĪ Īňš“—ŐżĻżńŕ≤ŅīęīÔ£¨Ņ… «ő“√«≤Ľń‹ő•∑īÕ‚ ¬ľÕ¬…£¨ŌÚňŻ√«Õł¬∂»őļőŌŻŌĘ°£
°°°°Ķ√÷™°įŃ÷ĪŽ ¬ľĢ°ĪłÝŃň“Ńőńňľļ‹īůĶńīÚĽų£¨ňŻļůņī–īĶņ£ļĶĹĶ◊ ≤√ī≤Ň « ¬«ťĶń’śŌŗ£Ņ’‚“Ľ ¬ľĢĶń’Ģ÷ő“‚“Ś « ≤√ī£Ņ
°°°°1977ńÍ2‘¬£¨“∂Ĺ£”ĘĹ”ľŻ“Ńőńňľ£¨—Ż«ŽňŻļÕ¬ÍňĻŃ’ņī÷–Ļķį≤∂»ÕŪńÍ£¨Ķę“Ńőńňľ“‘ņŽŅ™∑®ĻķĹę»Ī…ŔŌŻŌĘ«ĢĶņ°Ęń—“‘ī” ¬ľÕ¬ľ∆¨Ňń…„ő™”…–ĽĺÝŃň°£
°°°°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ļů£¨“Ńőńňľ◊‚◊°‘ŕįÕņŤľÚ¬™ĶńĻę‘ĘņÔ£¨ ß“Ķ ģńÍ°£°į÷Ľń‹“ņŅŅő“√«◊§∑® ĻĻ›łÝňŻĹ‚ĺŲ“Ľ–©ĺ≠ľ√ļÕ…ķĽÓő Ő‚°£°Ī¬ĹňŐļÕłśňŖ°∂÷–Ļķ–¬őŇ÷‹ŅĮ°∑°£
°°°°ĶęÕŪńÍĶń“ŃőńňľļÕ¬ÍňĻŃ’»‘»ĽŌŗ–Ň£¨°∂”řĻę“∆…Ĺ°∑≤Ę∑«»ň√«»Ōő™Ķńń«—ý£¨ «“Ľ≤Ņ–ťőĪĶń◊ų∆∑°£¬ÍňĻŃ’‘ÝňĶ£ļ°įő“Ōŗ–ŇĶĪ ĪĶń÷–Ļķ»ňĶń»∑ «‘ŕҨѶ ĶŌ÷’‚łŲőŕÕ–įÓ£¨ňŻ√«◊‘ľļ“≤ «Ōŗ–Ň’‚łŲőŕÕ–įÓĶń°£°Ī
°°°°“ŃőńňľňĶ£ļ°į’ś«ť ĶŅŲ÷Ľń‹Ĺ”ĹŁ£¨ňŁī”ņī≤Ľ «ĺÝ∂‘Ķń£¨ňŁĶńňń÷‹”––Ū∂ŗ“Úňō°£Ķę «ő“√Ľ”–ňĶ Ķ«ť÷ģ Ķ«ťĶń…›ÕŻ£¨ő“ŌŽňĶ√ųĶń «ő“√«ī”ņī√Ľ”–ÕśŇ™’ś«ť ĶŅŲ°£°Ī °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