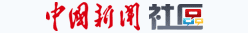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√Ů◊Ś“Űņ÷≤ł”ż≥Ųņ÷Ő≥…ŮĪ °°°°
°Ų ≤…∑√”°Ōů
°°°°Ĺ‹≥ŲĶń“Űņ÷ «ŐžŰ•÷ģ…ý£¨ľ§Ķī◊Ň»ňĶńŃťĽÍ°£
°°°°∂ŗ…Ŕīő£¨ĪĽ°∂ļžłŖŃĽ°∑Ķń°įĺ∆…Ů«ķ°Ī°Ę°∂ňģšį°∑Ķń°įļ√ļļłŤ°Ī°Ę°∂īů’¨√Ň°∑Ķń°įĶņ«ť°Ī£¨ĽĻ”–°∂īůļžĶ∆ŃżłŖłŖĻ“°∑°Ę°∂«Ôĺ’īÚĻŔňĺ°∑Ķ»Ķń”į ”“Űņ÷£¨’ūļ≥Ķ√–ńŃť∑Ę≤Ł°£į›∑√°įņ÷Ő≥…ŮĪ °Ī’‘ľĺ∆Ĺ£¨“Ľ÷Ī «ő“–ń÷–Ľ”÷ģ≤Ľ»•Ķń‘łÕŻ°£
°°°°2011ńÍ4‘¬£¨’ż÷Ķ‘Áīļ ĪĹŕ£¨”–ĽķĽŠņīĶĹőųį≤£¨»Á‘ľįīŌž√ŇŃŚ£¨“Ľ…ý«◊«–Ķń°į«ŽĹÝ°Ī£¨’‘Ō»…ķ“żŃžő“◊ŖĹÝňŻĶń ť∑Ņ°£ĶĪő“”Ž’‚őĽ÷Ý√Ż◊ų«ķľ“°Ę÷–Ļķ“Űņ÷ľ“–≠ĽŠ÷ųŌĮ√ś∂‘√ś◊ÝŌ¬ Ī£¨ő“∑ĘŌ÷’‚őĽ…Ū◊Ň≤ōņ∂…꼙∑Ģ°Ęī»√ľ…∆ńŅĶń“Űņ÷ľ“£¨”Žő“ŌŽŌů÷–“Ľ…Ūļņ∆Ý°Ę»ÁĻōőųīůļļĶń’‘ľĺ∆ĹÕÍ»ę≤ĽÕ¨£¨√ĽŌŽĶĹ£¨ňŻ «»Áīňő¬őń∂Ż—Ň£¨≥š¬ķŃň ťĺŪ∆Ý°£
°°°°ňŻĶń—Řĺ¶ļ‹ŃŃ£¨ńż÷ō∂Ý…ÓŚš°£»√ń„–ń÷–ľ§∑Ę≥ŲŐĹĪ¶Ķńļ√∆ś°£
°°°°ő“ňĶ£¨ńķ’‚«ķĹ≠Ľ™łģ–°«ÝĶńĽ∑ĺ≥’ś≤ĽīŪ£°
°°°°ňŻňĶ£¨ «į°£¨ĶĪ≥ű¬Ú’‚∑Ņ◊”≤Ň5000∂ŗ‘™“Ľ∆Ĺ∑Ĺ√◊°£“Úő™‘ŕ≥«Õ‚£¨”––©»ňĺűĶ√∆ę∆ß°£Ņ…’‚ņÔĶńĽ∑ĺ≥∂ŗļ√į°£°ÕýĪĪ£¨ĹŰŃŕīů—„ňĢ£¨ń« «Ő∆–Ģř »•őųŐž»°ĺ≠Ķń∆ūĶ„£¨“≤ «ňŻ∑ĶĽōĶń÷’Ķ„°£ňŻ‘ŕīů—„ňĢ∑≠“Ž’ŻņŪĺ≠őń£¨łÝ“Ľ…ķĽ≠…ŌŃň‘≤¬ķĶńĺšļŇ°£ÕýńŌ£¨ «÷’ńŌ…Ĺ£¨Ő∆īķ ę»ňÕűő¨°Ęį◊唓◊Ķ»‘Ý…ķĽÓ‘ŕ’‚“ĽīÝ£¨Õűő¨–īŃň≤Ľ…Ŕ√ŤĽś÷’ńŌ…ĹĶń ę£¨°∂÷’ńŌ…Ĺ°∑°Ę°∂÷’ńŌĪū“Ķ°∑°≠°≠į◊唓◊‘ŕŌ…”őň¬–īŃň°∂≥§ļřłŤ°∑°£«ķĹ≠’‚Ķō∑Ĺ‘ŕŐ∆īķ «őńĽĮ≥°ňý£¨¬•Ő®Õ§łů–°«ŇŃųňģ£¨őń»ň…ßŅÕĽŠľĮ”ŕīň£¨“ų ę◊ųł≥‘ōłŤ‘ōőŤ°£’‚łĹĹŁĽĻ”–Ő∆≥««Ĺ“Ň÷∑°Ęīů√ųĻ¨“Ň÷∑°≠°≠
°°°°ňĶ∆ūőųį≤ĶńĶō”ÚőńĽĮ£¨’‘ľĺ∆Ĺ»Á żľ“’š£¨Ŕ©Ŕ©∂ÝŐł°£’‚Ņīň∆ņŽŅ™≤…∑√÷ųŐ‚ĶńŌ–Ńń£¨∆š Ķ£¨’żī”“ĽłŲ≤ŗ√ś«–÷–Ńňő“–ń÷–ĶńĻō«–°™°™
°°°°Ŕľīů“ĽłŲ÷–Ļķ£¨—ß“Űņ÷ł„“Űņ÷Ķń»ňļ‹∂ŗ°£ő™ ≤√ī£¨ňŻń‹ĻĽ°įļžĪť»ęĻķ£¨◊ŖŌÚ ņĹÁ°Ī£ŅĪĽ”Ģő™°į◊ÓĺŖ∂ę∑Ĺ…ę≤ ļÕ÷–Ļķ∑ÁłŮĶń◊ų«ķľ“°Ī£Ņő™ ≤√ī£¨ňŻĶń“Űņ÷ń‹łÝ”į ”◊Ę»ŽŃťĽÍ£¨ ĻĶÁ”įļÕĶÁ ”ĺÁ“ÚňŻĶń“Űņ÷ļÕłŤ«ķ∂Ý√Ż—Ôňńļ££Ņő™ ≤√ī£¨ňŻĶń◊ų∆∑∂ŗīőĶ«…ŌĻķľ ņ÷Ő≥£¨≥…ő™Ļķńŕ°įĽ™ń…«©‘ľĶŕ“Ľ»ň°Ī£Ņő™ ≤√ī£¨ī”ĻŇ≥«őųį≤◊Ŗ≥Ų“ĽőĽ÷–Ļķ“Űņ÷ľ“–≠ĽŠ÷ųŌĮ£Ņ∂Ý«“£¨ňŻ“ņ»ĽĺžŃĶ◊Ň’‚◊ý≥« –£¨ńĢ‘ł‘ŕĪĪĺ©”Žőųį≤÷ģľšÕý∑ĶĪľ≤®£Ņ
°°°°ňŻňĶ£¨“Ľ∑ĹňģÕŃ—Ý“Ľ∑Ĺ»ň£¨ «»ż«ōīůĶō◊Ő—ÝŃňő“°£ő“ «őŁňĪ√Ů◊Ś“Űņ÷Ķń»ť÷≠£¨¬ż¬ż≥§īůĶń°£ő““’ ű…ķ√ŁĶńłý£¨‘ķ‘ŕ’‚∆¨ő÷ÕŃ£¨‘ű√īń‹ņŽĶ√Ņ™£ŅĽ∆ĶŘŃÍ”–“Ľ÷Í°įĻŇįōÕű°Ī£¨Ōŗīę «–ý‘ĮĽ∆ĶŘňý‘‘£¨“Úő™‘ķłýļ‹…Ó£¨÷ŃĹŮ÷¶∑Ī“∂√Į°≠°≠
°°°°…¬őų «łŲ…Ů∆śĶńĶō∑Ĺ£¨łī‘”Ķń◊‘»ĽĽ∑ĺ≥£¨‘žĺÕŃň»ňőńīę≥–Ķńłī‘”–‘ļÕ∂ŗ—ý–‘°£»ÁĻŻňĶ…¬ĪĪ «łŖŅļĶńļņ∑ŇŇ…£¨…¬ńŌļļ÷–°Ęį≤ŅĶĺÕ «“ű»ŠĶńÕŮ‘ľŇ…£¨Ļō÷–‘Ú «ľĮīů≥…÷ģĶō°£ ģ»ż≥ĮĻŇ∂ľ£¨őńĽĮĽżĶŪļŮ ĶĶ√őř∑®–ő»›°£ľł ģ÷÷Ķō∑ĹŌ∑°Ę…ŌįŔ÷÷√ŮłŤ√ŮĶų£¨»ÁīňłĽ»ńĶń“Űņ÷ňō—Ý£¨≤ł”żŃň“ĽłŲ’‘ľĺ∆Ĺ°£
°°°°’‘ľĺ∆ĹĶńłł«◊ «ĻķĽ≠īů ¶°Ę≥§į≤Ľ≠Ň…ĶńĶžĽý»ň’‘ÕŻ‘∆°£ňŻňš»Ľ√Ľ”–◊”≥–łł“Ķ£¨łł«◊»ī «ňŻĶ«…Ōņ÷Ő≥Ķń÷ł¬∑»ň°£’‘ľĺ∆Ĺ1964ńÍŅľ»Žőųį≤“Űņ÷—ß‘ļ£¨1970ńÍĪŌ“Ķ∑÷ŇšĶĹ °Ō∑ĺÁ—–ĺŅ‘ļ°£ňŻńÍ«Š∆Ý Ę£¨»»—™∑–Őŕ£¨”Ż‘ŕīī◊ų…Ōīů’Ļ≤ŇĽ™°£łł«◊ňĶ£¨ŌŽŇ‹Ņž£¨Ō»◊Ŗļ√√ī°£ń« «Ō∑ő—◊”£¨ļ√Ķ√ļ‹£¨ń„Ō»Ō¬»•į—Ķō∑ĹŌ∑—ß√ųį◊√ī°£”ŕ «£¨ňŻ“ĽÕ∑‘ķŌ¬»•£¨’Ż’ŻŇ‹Ńň21ńÍ£°łų÷÷Ķō∑ĹŌ∑ļÕ√ŮłŤ√ŮĶų£¨ňŻņ√ ž”ŕ–ńŃň°≠°≠
°°°°‘ŕīŚÕ∑°Ę‘ŕŐÔľš°Ę‘ŕ…Ĺ∆¬…ŌŐż√Ůľš“’»ň≥™Ō∑°Ę≥™łŤ£¨‘ŕ“§∂īņÔłķņŌŌÁŃńŐž£¨ «’‘ľĺ∆Ĺ◊ÓĹÚĹÚņ÷ĶņĶń√ņļ√Ľō“š°£ňŻňĶ£¨’‚21ńÍĶńĽżņŘ∂‘ő“Ķń»ň…ķŐę÷ō“™Ńň°£‘ŕ“’ ű…Ō£¨ő“”Ž√Ů◊Ś“Űņ÷Ķń—™¬ŲĻŠÕ®Ńň£Ľ‘ŕ«ťł–…Ō£¨ő“”Ž∆’Õ®įŔ–’ļÕ»ň√ŮĶń–ńĹŰĹŰŌŗѨ£¨ő“÷™ĶņňŻ√«ŌŽ ≤√ī£¨–Ť“™ ≤√ī°£ő“ĺűĶ√£¨ő“ «√Ů◊Ś“Űņ÷Ķń∂ý◊”£¨“≤ «»ň√ŮĶń∂ý◊”£¨ĺÕ «’‚÷÷∑«≥£«◊«–Ķńł–ĺű°£ňý“‘£¨√ŅĶĪő“◊Ý‘ŕł÷«Ŕ«į£¨ī” ¬īī◊ų£¨—Ř«įĺÕł°Ō÷≥ŲňŻ√«Ķń…Ū”įļÕ∆ŕŇőĶń—Ř…Ů°£≤Ľ“™∂ŃŃňľłĪĺ—ů ť£¨ ∂Ķ√—ů∆◊◊”ĺÕ◊‘«Š◊‘ľķ°£√Ů◊Ś“Űņ÷ «ő“√«őįīůĶńĪ¶Ņ‚£¨ő“√«“™ ōĽ§ļ√◊‘ľļĶńĺę…Ůľ“‘į°£Ņīň∆“ĽłŲļ‹ÕŃĶń∂ęőų£¨ł„≥ŲņīĺÕ”–ĽĮłĮ–ŗő™…Ů∆śĶńų»Ń¶°£
°°°°’‘ľĺ∆ĹĺÕ”–’‚łŲ…ŮĻ¶£¨Ī»»Á°∂ļžłŖŃĽ°∑£¨”√30÷ßŖÔńŇ°Ę4÷ßůŌ°Ę“Ľ◊ý÷–ĻķīůľżĻń◊ŗ√ý£¨“Ľ…ý°į√√√√ń„īůĶ®ĶōÕý«į◊ŖÕŘ°ĪĺÕį—…ķ√ŁĶńńŇļįÕīŅžŃ‹ņžĶōĪŪŌ÷≥Ųņī°£°∂ňģšį°∑÷–ňŻį—…Ĺ∂ęĶō∑Ĺ–°Ķų°∂ĺ‚īůł◊°∑–Ň ÷ńťņī£¨≥…ĺÕŃňŌž≥Ļ…Ů÷›Ķń°∂ļ√ļļłŤ°∑°£°∂īů’¨√Ň°∑ĺ©‘ŌŇ®”Ű£¨°∂««ľ“īů‘ļ°∑ĶńĹķļķļÕ∂ĢĻ…Ō“įť◊ŗĹķő∂ ģ◊„°≠°≠
°°°°ľ«’Ŗ≤…∑√ Ī£¨’‘ľĺ∆Ĺ’ż√¶”್ĺÁ°∂į◊√ęŇģ°∑Ķń“Űņ÷īī◊ų°£’‚ «”…∂ę∑Ĺ—›“ŚľĮÕŇļÕĻķľ“īůĺÁ‘ļŃ™ļŌ÷∆◊ųĶńŌ◊ņŮĺÁńŅ£¨Ĺę‘ŕ«ž◊£Ĺ®Ķ≥ĺŇ ģ÷‹ńÍ÷ģľ ‘ŕĪĪĺ©Ļę—›°£“’ ű◊‹ľŗľś…ýņ÷÷łĶľÕűņ•°Ę◊‹Ķľ—›ļķ√Ķ°Ę“Űņ÷◊‹ľŗ’‘ľĺ∆Ĺ°£
°°°°ňŻňĶ£¨°∂į◊√ęŇģ°∑ «ľ“”ųĽßŌĢĶńļž…ęĺ≠Ķš£¨”––Ū∂ŗŽŕ÷ň»ňŅŕĶńĺ≠Ķš≥™∂ő“™Ī£ŃŰŌ¬ņī£¨”––©“Űņ÷“™◊ŲĶų’Ż£¨°∂–Ú«ķ°∑“™◊Ų–¬Ķń£¨į—Ō÷īķ√ņł–”Žĺ≠Ķš“Űņ÷‘™ňō»ŕļŌ∆ūņī°£ Īľšļ‹ĹŰ£¨—ĻѶļ‹īů°£◊ųő™“Űņ÷»ň£¨īī◊ų «ő“Ķń Ļ√Ł°£ņŽŅ™«ŔľŁļÕņ÷∆◊£¨ő“–ńņÔĺÕ≤ĽŐ§ Ķ°£ ōĽ§√Ů◊Ś“Űņ÷Ķńĺę…Ůľ“‘į «ő“ĶńŐž÷į°£‘ŕīę≥–÷–ļŽ—Ô√Ů◊Ś“Űņ÷Ķń…Ů≤…£¨ł≥”ŤňŁŌ÷īķĽĮĶń…ķ√Ł’ŇѶ£¨»√ňŁ≥™Ōž ņĹÁņ÷Ő≥°£ő“‘ł“‚ő™Ńň’‚łŲ√őŌŽ£¨ĺŌĻ™ĺ°īŠ°£
°°°°°Ų ’‘ľĺ∆ĹľÚĹť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¨1945ńÍ…ķ»ň£¨őųį≤“Űņ÷—ß‘ļ‘ļ≥§£¨÷–Ļķ“Űņ÷ľ“–≠ĽŠ÷ųŌĮ°£…ŌłŲ ņľÕ80ńÍīķ‘ŕ”į ”“Űņ÷°įĪ¨∑Ę°Ī£¨≥…ő™ĽŮĹĪ◊Ó∂ŗ°ĘĹĪŌÓ◊ÓłŖĶń“Űņ÷ľ“°£ĶÁ”į°∂ļžłŖŃĽ°∑ĽŮĶŕįňĹž°įĹūľ¶°ĪĹĪ◊Óľ—◊ų«ķĹĪ£Ľ°∂őŚłŲŇģ◊”ļÕ“Ľłý…Ģ◊”°∑ĽŮ∑®Ļķ°įńŌŐō°ĪĻķľ ĶÁ”įĹŕ◊Óľ—“Űņ÷ĹĪ£ĽĶÁ ”ĺÁ°∂ňģšįīę°∑ĽŮĶŕ ģŃýĹž°į∑…Őž°ĪĹĪ◊Óľ—“Űņ÷ĹĪ£¨∆š÷–°įļ√ļļłŤ°ĪĽŮ◊Óľ—łŤ«ķĹĪ°£»’ĪĺJVC≥™∆¨ĻęňĺÕ∆≥Ųľ§Ļ‚≥™∆¨°∂Ľ∆ļ”“£“£°∑ľįŌĶŃ–ĶÁ”įľ§Ļ‚≥™∆¨£¨Ņ™÷–ĻķĶÁ”į“Űņ÷◊ŖŌÚ ņĹÁ÷ģŌ»ļ”°£√ņĻķĽ™ń…°§ŐōĶ√ŅňĻŇĶš≥™∆¨Ļęňĺ≥ŲįśňŻĶń≥™∆¨‘ŕ»ę«Ú∑Ę––°£’Ň“’ńĪ∆ņľŘ£ļňŻ «÷–ĻķĶĪīķ“Űņ÷ĶńņÔ≥ŐĪģ°£
°°°°≥’√‘“Űņ÷√Ł÷–◊Ę∂®
°°°°ľ«’Ŗ£ļ‘Ř÷–Ļķ»ňĶńīęÕ≥£¨ň∆ļűļ‹‘ŕ“‚◊”≥–łł“Ķ£¨∆š Ķ «ľ“Õ•Ľ∑ĺ≥Ķń—¨Ő’£¨ĺÕŌŮńķĶń∂ý◊”Ō÷‘ŕ“≤ł„“Űņ÷“Ľ—ý°£ńķłł«◊ «ĻķĽ≠īůľ“£¨∂‘ńķ”įŌžļ‹īů£¨ńķő™ ≤√ī√Ľł„√ņ ű∂Ý≥…ő™Ńň“Űņ÷ľ“£¨”–√Ľ”– ≤√ī°įī•Ķ„°Ī£¨ Ļńķįģ…Ō“Űņ÷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”–Ķńőń’¬ňĶő“…Ō–°—ß»żńÍľ∂Ķń ĪļÚ£¨‘૶Ī ļ–…Ō–īŃň“ĽłŲ÷ĹŐű£ļő“≥§īů“™◊Ų“Űņ÷ľ“°£’‚ «≤Ľ◊ľ»∑Ķń£¨—›“ÔŃň°£
°°°°ő“ī”–°ĺÕŌ≤Ľ∂“Űņ÷°£ļůņīĽōŌŽ£¨ő“Ķńņ÷ł–Ņ…ń‹ «”Ž…ķĺ„ņīĶń°£ń« Ī£¨ľ“ņÔļĘ◊”∂ŗ£¨ő“√«–÷√√8łŲ£¨łłńł“≤≤ĽĻ‹ń„Ō≤Ľ∂ ≤√ī°£≤ĽŌŮŌ÷‘ŕĶńńÍ«Šłłńł£¨ī”Ő•ĹŐŅ™ ľĺÕ∂®ŌÚŇŗ—ÝŃň°£Ļň≤ĽŃň’‚√ī∂ŗ°£ő“√«–÷√√łų”––ň»§£¨ő“ĺÕ◊Ň√‘“Űņ÷°£ĶĹ…ŔńÍĻ¨≤őľ”ĽÓ∂Į£¨ŐżľŻł÷«ŔĶĮ◊ŗĺÕ◊Ŗ≤Ľ∂Į¬∑Ńň£¨ĺÕĪĽőŁ“żŃň£¨ĺÕ≥’√‘ĶōŐż£¨ŇŅ‘ŕīįĽß…ŌŅī°£ń« Īľ“ņÔ«Ó£¨≤ĽŅ…ń‹”–ł÷«Ŕ£¨ń‹¬Ú÷ĽŅŕ«ŔĺÕ≤ĽīŪŃň°£
°°°°’ś ĶĶń«ťŅŲ «£¨ő“√«°įŃý“Ľ°Ī∂ýÕĮĹŕł„ůŰĽūÕŪĽŠ£¨ņŌ ¶»√√ŅłŲÕ¨—ßňĶňĶ◊‘ľļĶńņŪŌŽ°£ő“ňĶ£¨ő“≥§īů“™ĶĪłŲ“Űņ÷ľ“°£“≤√Ľ”– ≤√ī ¬«ťĶń°įī•∂Į°Ī£¨ĺÕ «ī”–ńņÔŌ≤Ľ∂°£ő“–° ĪļÚĺÕŐōĪūįģŐżŌ∑£¨◊‘ľļĺÕ»•Ō∑‘ļŐżŌ∑Ńň°£’‚ « ‹łł«◊Ķń”įŌž£¨ňŻ∑«≥£Ō≤Ľ∂ŐżŌ∑£¨∂Ý«“£¨łķ–Ū∂ŗ—›‘ĪĻōŌĶļ‹ļ√°£ő“ľ«Ķ√ļ‹«Ś≥Ģ£¨Ī»»Á£¨…––°‘∆√ŅłŲ–«∆ŕŐž≤Ó≤Ľ∂ŗ∂ľĶĹő“√«ľ“ņī°£ő“łķ…–≥§»Ŕ‘ŕ“ĽŅť∂ýÕś£¨∂ľ «≥∆–÷ĶņĶ‹Ķń°£‘ŕ’‚—ýĶńĽ∑ĺ≥÷–∂ķŚ¶ńŅ»ĺ£¨∂‘’‚–©īęÕ≥“Űņ÷ĺÕ∑«≥£ žŌ§Ńň£¨”–ļ‹…ÓĶń”°Ōů°£ī”“Ňīę—ßĶńĹ«∂»Ņī£¨łł«◊√Ľ”–į—√ņ űĽý“ÚīęłÝő“£¨»īį—“Űņ÷Ľý“ÚīęłÝŃňő“°£“≤–Ū£¨ő“ĺÕ «√Ł÷–◊Ę∂®“™ł„“Űņ÷£¨ĺÕ «ļ‹◊Ň√‘°£
°°°°Ň‹Īť»ż«ōŅŗ÷–”–ņ÷
°°°°ľ«’Ŗ£ļńķį—≥…Ļ¶ĻťĹŠ”ŕ“’ űĽżņŘļÕ…ķĽÓĽżņŘĶńļŮĽżĪ°∑Ę£¨ńķ‘ŕŌ∑ĺÁ—–ĺŅ‘ļ21ńÍ£¨Ň‹ĪťŃň»ż«ōīůĶō°£ĶĪ ĪŐűľĢń«√īľŤŅŗ£¨ « ≤√īѶŃŅ÷ß≥Ňńķ’‚√ī“Ľ¬∑Ň‹Ō¬ņī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ňĶ ĶĽį£¨ĶĻ“≤√ĽĺűĶ√”– ≤√īŐōĪūĶń°įĺę…Ů÷ß≥Ň°Ī°£ ◊Ō»ń« «Ļ§◊ų£¨ő“ «÷łĽ”£¨’‚ĺÕ“™«ůń„£¨ĺÁÕŇ◊ŖĶĹńń∂ý£¨ń„Īō–Ž◊ŖĶĹńń∂ý°£ĺÁÕŇ¬Ô£¨∂ľ «√ŅŐžÕŪ…Ō—›Ō∑£¨į◊ŐžĺÕ√Ľ ¬°£łł«◊ĶńĽį£¨“Ľ÷Ī◊į‘ŕő“–ńņÔ°£“™ŌŽŇ‹£¨Ō»—߼Š◊Ŗ°£’‚łŲ£¨ő“…Ó”–ŐŚĽŠ°£łł«◊ňś ÷ÕŅń®£¨ĺÕ «“Ľ∑ýļ‹√ņĶń…ĹňģĽ≠°£ő“√ĽŃ∑ĽýĪĺĻ¶£¨Ľ≠≤ĽŃň£¨“≤Ľ≠≤Ľ≥…°£ő“÷™Ķņ£¨Őżłł«◊ĶńĽį£¨√ĽīŪ°£į◊Őž£¨ő“ĺÕĶĹīŚ’ÚņÔ◊Ŗ◊Ŗ£¨ňńī¶ŐżŐż√ŮłŤ°Ę√ŮĶų°£’“√ŮľšĶń“’»ňŃńŐž£¨ŐżňŻ√«ňĶłŤ°ĘňĶŌ∑°£ő“∂‘’‚–©ŐōĪū”––ň»§£¨Őż◊ŇĻżŮę£¨»Ō»Ō’ś’śľ«‘ŕĪĺ◊”…Ō£¨Ľż‘‹Ńňľł ģĪĺňō≤ń£¨◊įŃň¬ķ¬ķ“ĽŌš◊”°£ő“∑«≥£‘ł“‚’‚—ý◊Ų°£
°°°°’‚»∑ Ķ «“Ľ÷÷ĽżĶŪ£¨”»∆š «…ŌłŲ ņľÕ70ńÍīķĶĹ80ńÍīķ£¨’‚10ńÍ£¨ő“√«Ō¬ŌÁŌ¬Ķ√Ī»ĹŌņųļ¶°£‘ŕ’‚∆ŕľš£¨≥…Őž√¶”ŕ—›≥ŲļÕ≤…∑Á£¨≤ĽŅ…ń‹ł„∆šňŻīī◊ų£¨ĽýĪĺ…ŌĺÕ «‘ŕ—ßŌį°£ő“√«Ō¬»•ĺ≠≥£◊°‘ŕīŚ◊”ņÔ°ĘņŌŌÁľ“£¨ňš»ĽŐűľĢľŤŅŗ£¨ĶęŅŗ÷–ń„Ņ…“‘’“ĶĹļ‹∂ŗņ÷»§°£
°°°°ņ÷»§ « ≤√ī£ŅĺÕ «ń„Ņ…“‘ĺ≤Ō¬–ńņī—ßŌį£¨ń„Ņ…“‘ĺ≤Ō¬–ńŃňĹ‚’‚łŲ…ÁĽŠ◊ÓĶ◊≤„Ķń…ķĽÓ£¨—ßŌį√ŮľšĶń“’ ű£¨’‚ĺÕ «“Ľ÷÷ĽżņŘ°£ĪūĻ‹∂ŗ√¶∂ŗņŘ£¨ő““≤į—ŐżĶĹ°Ę—ßĶĹ°Ęł– ‹ĶĹĶń∂ęőų’ŻņŪ≥Ųņī£¨‘ŕ√ļ”ÕĶ∆Ō¬£¨∂¨Őž ÷∂≥Ķ√∑Ęńĺ£¨ŌńŐžő√≥ś∂£“ß°≠°≠ő“į——ßĶĹĶń∂ęőųĶĪ≥…Ī¶Īī£¨ĺÕĺűĶ√◊‹”–“ĽŐžňŁĽŠŇ……Ōīů”√≥°°£ňý“‘£¨ Īľš“ĽĶ„∂ý“≤√Ľņň∑—£¨»ę”√‘ŕ—ßŌį…ŌŃň°£
°°°°ľ«’Ŗ£ļĶĪ ĪŐűľĢ”–∂ŗľŤŅŗ£¨ńķĽĻ”–”°Ōů¬ū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»ňĺÕ «’‚—ý£¨÷Ľ”–ŌŪ≤ĽŃňĶńł££¨√Ľ”–≥‘≤ĽŃňĶńŅŗ°£Ō÷‘ŕ»ň√«Ņ…ń‹ĺűĶ√ń«ļ‹Ņŗ£¨ĶĪ ĪĽĻ’ś√ĽĺűĶ√”–∂ŗŅŗ°£”– ĪňĮ‘ŕ“§∂īĶńīůÕ®∆Ő…Ō£¨”– ĪĺÕňĮ‘ŕ–°—ßĹŐ “ņÔ£¨Ń¨łŲ»°ŇĮĶń¬Į◊”“≤√Ľ”–°£į—Ķ ◊”°ĘŅő◊ņ“Ľ∆ī£¨∆Ő…Ō–©¬ů≤›£¨ĺÕ «ī≤Ńň°£Ņő◊ņ≤ĽĻĽ£¨ĺÕį—≤›Ķś◊”ĽÚ¬ů≤›∆Ő‘ŕĶō…Ō£¨īůľ“ľ∑‘ŕ“Ľ∆ū£¨ĽĻń‹ŇĮļÕ“ĽĶ„∂ý°£ŌńŐž£¨ő√≥śĶń∂£“ßļ‹ņųļ¶£¨ő“√«ļ»Ķńňģ£¨īůľ“Ĺ–°į”¨◊”Őņ°Ī°£≤‘”¨őňőňĶń≥…»ļĹŠ∂”£¨…Ĺ«Ý÷Á“Ļő¬≤Óļ‹īů£¨ń„‘Á≥Ņ…’Ņ™ňģ£¨”¨◊”∂ľŇŅ‘ŕĻÝĪŖĶń«Ĺ…ŌŃň£¨ňģ“ĽŅ™£¨»»∆ÝŐŕŐŕ£¨≤‘”¨ĺÕ÷ůĶĹņÔ√ś£¨ņŐ≥Ųņī£¨ňģ’’—ýļ»£¨◊‹Ī»ļ»…ķňģ«Ņ°£≥ī≤ň°Ęįĺ÷ŗ£¨“≤≥£”–≤‘”¨°≠°≠“≤Ļ÷£¨ĺĻ»Ľļ‹…Ŕ”–ņ≠∂«◊”Ķń°£
°°°°ĻŠÕ®—™¬ŲĻůĪ»Ľ∆Ĺū
°°°°ľ«’Ŗ£ļń« Īł„“’ űĶń»ň£¨Ō¬Ľý≤„—›≥Ų°Ę≤…∑Á£¨’ś «”ŽņŌįŔ–’Õ¨ł Ļ≤Ņŗ°£ő“≤…∑√’Ň»ū∑ľ Ī£¨ňżňĶŇń°∂ńŌ’ųĪĪ’Ĺ°∑ĺÕňĮ‘ŕ–°—ßĹŐ “ņÔ£¨≥‘”Ů√◊√ś‚ń‚ńīůī–’ļĹī£¨łķ»ň√Ůļ‹Őý–ń°£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∂‘£¨’‚÷÷ŐŚ—ťļÕł–őÚĪ»Ľ∆ĹūĽĻ’šĻů°≠°≠√Ľ”–’‚÷÷ĺ≠ņķĶń»ň£¨∂‘ņŌįŔ–’Ķń…ķĽÓ «√Ľ”––ńŃťł– ‹Ķń£¨ňŻ√«∂‘įŔ–’ «ł© ”£¨ «◊‘“‘ő™łŖĻůĶńÕýŌ¬Ņī°£ő“√«łķņŌįŔ–’ĶńĻōŌĶĺÕ≤Ľ“Ľ—ý£¨ňŻ√« «į—ő“√«ĶĪ◊‘ľ“»ň£¨ņ≠ń„◊Ý‘ŕŅĽÕ∑…Ō£¨łķń„ňĶ–ńņÔĽį£¨ņŌ“’»ňį—ňŻĶńÕś“‚∂ýļŃőřĪ£ŃŰĶō»ęŐÕłÝń„°£ő“ĺÕł–ĶĹłķ√Ů◊Ś“Űņ÷Ķń—™¬ŲĻŠÕ®Ńň£¨łķņŌįŔ–’Ķń–ńĹŰĹŰŌŗѨ°£
°°°°’‚—ý£¨ő“∂‘»ň√ŮĶńņŪĹ‚°Ę∂‘…ķĽÓĶńņŪĹ‚°Ę∂‘“Űņ÷ĶńņŪĹ‚£¨ĺÕ≤Ľ“Ľ—ýŃň°£ňý“‘£¨ĶĪő“ī” ¬“Űņ÷īī◊ųĶń ĪļÚ£¨—Ř«įĺÕĽŠł°Ō÷≥Ųń«–© žŌ§Ķń…Ū”į°≠°≠∂‘»ň√Ů°Ę∂‘įŔ–’…ķĽÓ£¨◊‘»Ľ∂Ý»ĽĺÕ”–Ńň“Ľ÷÷–ńŃťĶńĻō’’°£
°°°°ľ«’Ŗ£ļńķĶń’‚łŲĺ≠ņķļÕł–őÚŐę÷ō“™Ńň£°ő™ ≤√īĪū»ň√Ľ”–ńķĶń“Űņ÷≥…ĺÕ£ŅĪū»ň“≤—ß“Űņ÷£¨“≤ł„īī◊ų£¨ő™ ≤√īń—“‘ł„≥Ųĺ™ ņļßň◊ĶńĹ‹◊ų£¨≤ÓĪū“≤–ŪĺÕ‘ŕ’‚ņÔį…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ő“√«Ķń“Űņ÷ľ“īī◊ų≥Ų–Ū∂ŗ”Ň–„◊ų∆∑£¨∆š÷–≤Ľ∑¶ń„ňýňĶĶńĹ‹◊ų°£ő“Ķń◊ų∆∑őīĪō”–ń«√īļ√£¨ĽĻ «…Ŕ–©“Á√ņ÷ģī ļ√°£ĶĪ»Ľ£¨ő“‘ł“‚ŐĹŐ÷»Áļő≤Ňń‹īī◊ų≥Ų”Ň–„◊ų∆∑Ķńő Ő‚°£ő“ņŪĹ‚£¨—ßŌį”–ŃĹ÷÷£¨“Ľ÷÷ «—ßľľ űĽÚ’ŖĹ–—ßľľ«…£ĽŃŪ“Ľ÷÷ «‘ŕ—ßľľ«…ĶńĽýī°…Ō£¨—ß◊Ų»ň—ßł–«ť£¨Ľ≥Īß◊Ň»ň√ŮĶńīůŃťĽÍ°Ęīůĺę…Ů°£”Ž√Ů◊Ś“Űņ÷ļÕ»ň√Ů«ťł–Ķń—™¬ŲĻŠÕ®£¨Ī» ≤√ī∂ľ’šĻů£°√Ľ”––ńŃťĶń◊Ő—Ý£¨ĺÕ «ł……¨Ķń£¨ «ňņįŚĶń∂ęőų£¨√Ľ”– ≤√ī…ķ√ŁĶńĽÓѶ°£
°°°°◊ų∆∑ī”–ńņÔ°įŃų°Ī≥Ųņī
°°°°ľ«’Ŗ£ļńķ…∆”ŕ‘ŕ“Űņ÷īī◊ų÷–»ŕ»Ž∂ŗ÷÷“Űņ÷‘™ňō£¨‘ŕ“Ľ–©»ňŅīņī£¨ŌŮ∆ņĺÁ°Ęįū◊”’‚–©Ņ…ń‹ «∑Á¬ŪŇ£≤ĽŌŗľįĶń£¨ńķ»īń‹ĻĽį—ňŁ√«°į…ŮÕ®°Ī∆ūņī£¨Ō‘≥Ųńķ◊ų∆∑Őō”–Ķń°į…Ů∆Ý°Ī£¨’‚÷÷ĹŠļŌ»Áīň«…√Ó£¨ĺų«Ō « ≤√ī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√Ľ”–ĺų«Ō°£∆š Ķ£¨ő“‘ŕīī◊ųĻż≥Ő÷–£¨≤Ę√Ľ”–ŅŐ“‚Ķō◊∑«ů°£ňŁĺÕ «◊‘»Ľ∂Ý»Ľ°įŃų°Ī≥ŲņīĶń°£ő“√ĽŌŽń«√ī∂ŗ£¨“≤√ĽŌŽ”–ń«√ī∂ŗ«…√ÓĶń»ŕļŌ°£◊ų∆∑≥Ųņī£¨īůľ“∂ľł–ĺűļ√£¨»√∆ņ¬Řľ““Ľ∑÷őŲ£¨ĺÕŐűŐű «ĶņŃň°£’‚ «∆ņ¬Řľ“ņŪ–‘∑÷őŲĶńĹŠĻŻ°£∆š Ķ£¨ő“’ś√ĽŌŽń«√ī∂ŗ£¨»ÁĻŻīī◊ų ĪŌŽń«√ī∂ŗ£¨Ņ…ń‹ĺÕ–ī≤Ľ≥ŲņīŃň°£≤‹—©«Ř–ī°∂ļž¬•√ő°∑őīĪōŌŽĶĹń«√ī∂ŗ£¨ĶĹ°įļž—ßľ“°Īń«ņÔ“Ľ—–ĺŅ£¨ĺÕ «ļ√īůĶń—ßő Ńň°£
°°°°ő“ĶĪ ĪĺÕĺűĶ√’‚—ýĪŪīÔļ√£¨ĺÕ’‚—ý–īŃň£¨ĺÕ «ī”–ńņÔ◊‘»ĽĶńŃųŐ °£Ī»»Á°∂««ľ“īů‘ļ°∑£¨ő“–ī≥Ųņī“‘ļů£¨…ĹőųĹķĺÁ‘ļĶń»ňņī’“ő“£¨ňĶ’‘ņŌ ¶£¨ő“√«”–“Ľ≥ŲĹķĺÁ£¨ńķįÔ÷ķő“√«ł„“Ľł„°£ő“ňĶ£¨ő“≤ĽŐę∂ģ°£ňŻ√«ňĶ£¨°∂««ľ“īů‘ļ°∑ńķ–īĶ√ń«√īļ√£¨ĹķĺÁ“Úňō‘ň”√Ķ√ń«√īļ√£¨“Ľ∂®ń‹ł„°£ő“ňĶ£¨ő“ «∆ĺł–ĺű–īĶń£¨ĹķĺÁő“≤ĽŐę∂ģ£¨ł„≤ĽŃň°£»ÁĻŻ»√ő“Ň™«ō«Ľ°ĘÕŽÕŽ«Ľ£¨ń«––£¨“Úő™ő“∂ģ°£’‚∆š Ķ «“Ľ÷÷◊‘»ĽĶńĽżņŘ£¨ «ń„∂‘įū◊”«Ľń«÷÷◊‘»ĽĶńł–őÚ°£Ī»»Á£¨ĺ©‘ŌīůĻńļÕĺ©ĺÁ£¨ňŁ”Ô—‘Ķńńł”Ô «ņŌĪĪĺ©Ľį£¨ņŌĪĪĺ©ĽįĺÕŐ”≤Ľ≥ŲňŁ”Ô—‘ĶńĪĺŐŚ£¨ňý“‘£¨“Űņ÷…ŌňŁ «◊‘»ĽĶń∂ęőų°£◊ų«ķľ“≤Ľń‹ŐęĻŇįŚ£¨“™”–“Ľ÷÷Ńť–‘£¨‘ŕīī◊ų÷–“™”–Ńť–‘°£’‚—ý£¨ń„Ķń∂ęőų≥Ųņī£¨≤Ňń‹…Ó»ŽĶĹņŌįŔ–’–ńņÔ£¨≤Ňń‹īÚ∂ĮĪū»ň°£
°°°°’‚√īňĶį…£¨’‚–©“Űņ÷‘™ňō£¨“—ĺ≠Ńų∂Į‘ŕő“Ķń—™“ļņÔŃň°£ĶĹ–Ť“™Ķń ĪļÚ£¨ňŁĺÕŃųŐ ≥ŲņīŃň°£ń„»ÁĻŻ√Ľ”–’‚÷÷ł–«ť°Ę’‚÷÷ĽżņŘ°ĘĽĻ”–ŌŻĽĮőŁ ’ĶńĻż≥Ő£¨ĺÕ≤Ľń‹»ŕĹÝń„Ķń—™“ļņÔ°£ń«÷Ľń‹ «“Ľ÷÷°įĶĢľ”°Ī£¨ «»ňő™Ķń°į∂—∆Ų°Ī£¨ «…ķ”≤Ķń°Ę≤ĽŃų≥©Ķń°Ę√Ľ”–…ķ√ŁļÕŃťĽÍĶń°£°įĶĢľ”°Ī‘Ŕ∂ŗ“≤ «√Ľ∑®»ŕļŌĶń°£ĺÕŌŮ–ī–°ňĶ£¨◊ųľ“ňś◊Ň»ňőÔ√Ł‘ňĶń∑Ę’Ļ£¨ĺÕ’‚√ī–īŌ¬ņī£¨ĺÕ «ň≥∆š◊‘»Ľ£¨őń’¬Őž≥…°£
°°°°ő™Ńň∑Ī»Ŕ√Ů◊Ś“Űņ÷
°°°°ľ«’Ŗ£ļ»ÁĻŻ”√“ĽĺšĽįłŇņ®ńķĶń»ň…ķ◊∑«ůĽÚ’Ŗ»ň…ķņŪŌŽ£¨’‚嚼į « ≤√ī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”–»ňňĶő“ «ő™“Űņ÷∂Ý…ķĶń°£ő““≤ĺűĶ√£¨ «√Ł÷–◊Ę∂®ő“”Ž“Űņ÷ĹŠ‘Ķ“Ľ…ķ°£ő“»ŌÕ¨’‚łŲ∂ęőų£¨ĺÕ «ľÁłļ◊Ň“Ľ÷÷“Űņ÷»ňĶń Ļ√Łł–°£
°°°°ő“ĶńņŪŌŽ£¨ Ķľ …Ō «‘ŕ◊∑«ůő“łł«◊◊ŖĻżĶńĶņ¬∑£¨ňŻ‘ŕ√ŮľšĶńĶņ¬∑…ŌľŠ»Õ≤ĽįőĶō◊ŖĶĹ…ķ√ŁĶńĺ°Õ∑°≠°≠łł«◊“Ľ÷Ī…ķĽÓ‘ŕ√Ůľš£¨ő™ņŌįŔ–’∂Ýīī◊ų°£łł«◊ňĶ£¨ő“ «ŌÁľš»ň£¨Ľ≠ŌÁľšĶńĽ≠£¨ő™ŌÁľš»ň∑ĢőŮ°£ő“Ķń◊∑«ů Ķľ …Ōłķłł«◊ «“Ľ÷¬Ķń°£—ō◊ŇňŻĶńĶņ¬∑£¨ľŐ–ÝÕý«į◊Ŗ°£ő™∆’Õ®Ķńīů÷ŕ∑ĢőŮ£¨ő™ņŌįŔ–’∑ĢőŮ°£◊∑«ů◊ų∆∑Ķń»ň√Ů–‘£¨ «ő“–ń÷–ľ»∂®ĶńńŅĪÍ°£–ńņÔŌŽĶńĺÕ «“™–ī≥ŲņŌįŔ–’Ō≤őŇņ÷ľŻĶń∂ęőų°£“™—Ňň◊Ļ≤…Õ°£ľ»“™”–ļ‹łŖĶń“’ űňģ◊ľ£¨”÷“™”–Ō √ųĶń Īīķł–£¨◊ŲĶĹ’‚łŲļ‹ń—°£
°°°°“Űņ÷◊ų∆∑≤ĽĹŲ“™ĹÝ»Ž“Űņ÷ ∑£¨łŁ“™ĹÝ»Ž»ň–ń£¨”Ž»ň√ŮĶń–ń…ý≤ķ…ķĻ≤√ý£¨”Ž ĪīķĶń¬Ų≤ęÕ¨ŐÝ∂Į£¨’‚—ý≤Ňń‹≥…ő™ĺ≠Ķš°£ĺÕ «“™∑Ī»Ŕő“√«Ķń√Ů◊Ś“Űņ÷£¨ő“√«Ő∆īķĶń“Űņ÷őŤĶł «◊ÓłŖňģ∆Ĺ£¨‘Ýĺ≠Ļ‚“ę ņĹÁ°£√Ů◊ŚĹĽŌžņ÷°∂√őĽōīůŐ∆°∑£¨ĺÕľńÕ–◊Ňő“Ķń’‚łŲņŪŌŽ°£
°°°°–ĽĺÝł°‘Íĺ≤–ńīī◊ų
°°°°ľ«’Ŗ£ļńķŌ÷‘ŕ «÷–Ļķ“Ű–≠÷ųŌĮ£¨įī’’“Ľį„Ķń≥£ņŪ£¨ńķ”¶ł√Ļ§◊ų‘ŕĪĪĺ©°Ęĺ”◊°‘ŕĪĪĺ©£¨“ņ’’ŌŗĻōĻś∂®ļ√ŌŮĽĻ”¶ł√ŌŪ ‹≤Ņľ∂īż”Ųį…£Ņ
°°°°’‘ľĺ∆Ĺ£ļő“≤ĽŐę«Ś≥Ģ’‚–©∂ęőų£¨ő“≤Ľ∂ģ£¨“≤√Ľő Ļż°£ő“Ō÷‘ŕĺÕ «ŃĹĪŖŇ‹°£ĪĪĺ©ń«ĪŖłÝŃň∑Ņ◊”£¨“Ű–≠”–≥Ķ£¨≤Ľ «◊®≥Ķ£¨ő“‘ŕĪĪĺ© ĪŅ…“‘”√°£∂‘£¨ő“ļÕįģ»ň‘ŕĪĪĺ©ĽĻ”–◊°ī¶£¨Ķ»”ŕĪĪĺ©°Ęőųį≤ŃĹłŲľ“į…°£ĪĪĺ© « ◊∂ľ°Ę «’Ģ÷őőńĽĮ÷––ń£¨∑«≥£”–ų»Ń¶°£ł’≤ŇňĶĻż£¨ő“∂‘…¬őų’‚∆¨ÕŃĶōł–«ťŐę…Ó£¨…ÓĶĹőř∑®łÓ…Š°≠°≠
°°°°∂ŗńÍņī£¨ő“—Ý≥…‘Á∆ūīī◊ųĶńŌįĻŖ°£‘Á≥ŅĶń Īľš£¨∂‘ő“∑«≥£Ī¶Ļů£¨“™–ī∂ęőų°Ę“™∂Ń ť°£‘ŕ’‚ņÔ£¨ő“◊Ó„ę“‚Ķń «Ľ∑ĺ≥ļ√£¨Ī»ĹŌį≤ĺ≤£¨ń‹ĻĽ»√–ń∆Ĺĺ≤Ō¬ņī°£īī◊ų «–Ť“™ĺ≤Ō¬–ńņīĶń°£√¶”ŕ”¶≥Í£¨»ňĺÕł°‘ÍŃň°£
°°°°‘Ýĺ≠”–»ňő ő“£¨‘ű—ý≤Ňń‹–ī≥Ų”Ň–„◊ų∆∑£Ņő“ňĶ£¨◊ÓĻōľŁĶń£¨ł„īī◊ųĺÕĪō–Žĺ≤Ō¬–ńņī°£ń„“™ ō◊°’‚Ņť◊‘÷ųīī◊ųĶńĺę…Ůľ“‘į£°’‚∑«≥£÷ō“™°£Ō÷‘ŕ”––©»ň≤Ľ÷™Ķņ◊‘ľļ’ŻŐž√¶–©…∂£¨į•”ī£¨ń«łŲ»»ń÷£¨ ≤√īĽÓ∂Į∂ľÕýņÔī’»»ń÷£¨Ņī◊ŇĽĻÕ¶√¶°£“ĽńÍ√¶ĶĹÕ∑£¨ĹŠĻŻ£¨ ≤√ī“≤√Ľ°į√¶°Ī≥Ųņī°£
°°°°ő™ ≤√īŌ÷‘ŕ≥Ų≤Ľņī”Ň–„◊ų∆∑£Ņ√¶◊Ň”¶≥Í»•Ńň£¨’‚ĽĻ––£ŅĽĻ «“™ł ”ŕľŇńĮ£¨ő“÷™Ķņ’‚ļ‹ń—£¨÷‹őßĶńł…»ŇŐę∂ŗŃň°£»ÁĻŻ ≤√īĽÓ∂Įń„∂ľīū”¶£¨ ĪľšĺÕ√ĽŃň£¨ĺÕ ≤√ī“≤Ň™≤Ľ≥…Ńň°£«į–©Őž£¨ő“‘ŕĪĪĺ©ŇŲľŻŃň∑Žśų≤Ň£¨ňŻňĶ£¨Őę»»ń÷Ńň£¨’‚√ī√¶”ŕ”¶≥ÍŅ… ‹≤ĽŃň£¨‘Ř√«Ķń ĪľšŐęĪ¶ĻůŃň°£ő“√«∆ń”–Õ¨ł–°£ĶĪ»Ľ£¨ Ű”ŕ∑÷ńŕĶńĻ§◊ų «“Ľ∂®“™Ň¨Ń¶ł…ļ√Ķń£¨’‚“≤ «ő“Ķń‘≠‘Ú£¨≤Ľ”√—ÔĪř◊‘∑‹Ő„°£Ī»»Á£¨ł’≤Ňń„ŐŠĶĹĽ™ń…łÝő“≥Ų≥™∆¨£¨Ļķľ įś¬ŰĶ√ļ‹ļ√£¨ĻķńŕĶŃįśļ‹ņųļ¶°£Ļō”ŕĪ£Ľ§“Űņ÷÷™ ∂≤ķ»®Ķńő Ő‚£¨ő“ĺÕņŻ”√“Ľ«–ĽķĽŠļÕ ÷∂őňńī¶ļŰ”ű£¨”¶ł√ňĶĻķľ“Ō÷‘ŕ“—ĺ≠łŖ∂»÷ō ”Ńň£¨ÕÍ…∆∑®¬…∑®ĻśļÕľŗĻ‹÷∆∂»£¨Ī£Ľ§Ķńő Ő‚ĽŠĹ‚ĺŲĶń°£
°°°°ľ«’Ŗ –§«Ô…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