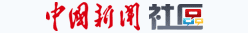°°°°“į≤›“Ľ—ýĶńÕĮńÍ°™°™–ī”ŕŌŰļžįŔńÍĶģ≥Ĺ÷ģľ
°°°°”ŲĶĹŌŰļž£¨ «1986ńÍ°£’‚“ĽńÍ3‘¬£¨ő“‘ŕ°∂…Ōļ£őń—ß°∑…Ō∑ĘĪŪŃň∂Ő∆™–°ňĶ°∂–°īį–ű”Ô°∑£¨–°ňĶ–ī“ĽłŲ«ŗńÍ‘ŕ≥«ņÔ∂ŃŃňŃĹńÍ ť÷ģļů‘ŔĽōĶĹŌÁŌ¬ľ“ņÔĶń∑≥ń’–ń–ų£¨ňżőŇ≤ĽĻŖŌÁīŚŃĶ»ň…Ū…ŌҮѓĶńĽĮ∑ ∆Ýő∂£¨Őż≤ĽĻŖńŐńŐ°Ęłłńł°ĘłÁ…©ňśĶōÕ¬ŐĶĶń…ý“Ű£¨Ņī≤ĽĻŖ∆Ő¬ķ‘ļ¬šĶńľ¶—ľ÷ŪĻ∑∑ŗĪ„£¨łŁ≤ĽĹ” ‹‘≠ņī”–◊Ň‘∂īůņŪŌŽĶńĻŽ÷–√‹”—“—ĹŠĽť…ķ◊”°ĘĪĽĽÓ…ķ…ķņ≠ĹÝńŗÕŃĶńŌ÷ Ķ°≠°≠ń« «“Ľ≤Ņ◊‘īęŐŚ–°ňĶ£¨ńŕ÷––Ū∂ŗ«ťĹŕ∂ľ «ő“Ķń«◊…Ūĺ≠ņķ£¨Ņ…ő“ŌŽ≤ĽĶĹ£¨ĺÕ «’‚—ý“Ľ∆™–°ňĶ∑ĘĪŪ÷ģļů£¨“ĽłŲ∂Ń’Ŗī”īůѨŅ™∑Ę«Ý≥Ų∑Ę£¨Ņ™≥Ķ◊®≥Őņī◊Įļ”ľŻő“°™°™ń« Ī“—ĺ≠”–ŃňŅ™∑Ę«Ý’‚—ýĶń–¬…ķ ¬őÔ£¨’‚őĽņī∑√’Ŗ «Ņ™∑Ę«ÝĻ‹őĮĽŠ“ĽőĽŃžĶľ°£ŃÓő“ŌŽ≤ĽĶĹĶń «£¨ňŻ…Ū‘ŕłńłÔŅ™∑Ň◊Ó«į—ō£¨»ī”–Ō–Ōĺ∂Ń–°ňĶ£¨≤Ę«“£¨ňŻĽĻīÝņī“ĽőĽ»»įģ–°ňĶĶńŇů”—£¨≤Ę«“£¨ňŻĶńŇů”—ĽĻīÝņīŃňľŻ√śņŮ°™°™ŌŰļžĶń°∂ļŰņľļ”īę°∑°£ĶĪ Ī£¨ő“łýĪĺ≤Ľ÷™ĶņŌŰļž «ň≠£¨≤Ľ«Ś≥ĢňŻ√«ő™ ≤√ī“™ňÕő“ňżĶń ť°£ń«≤Ľ « ť£¨ «“ĽĪĺłī”°ľĢ£¨ «ņī∑√’Ŗ◊®√Ňő™ő“łī”°Ķń°∂ļŰņľļ”īę°∑°£“Úő™≤Ľ÷™ĶņŌŰļž «ň≠£¨“≤ĺÕ≤Ľ÷™Ķņ’‚∑›ņŮőÔ”–∂ŗ√ī÷ō“™£¨≤ĽĶę»Áīň£¨”…”ŕł’ł’Ņ™ ľ–ī◊ų£¨ł’ł’“Úő™–ī◊ų∂Ýī”Ň©īŚ◊Ŗ≥Ų£¨ĶĹ◊Įļ”ŌōőńĽĮĻ›…Ōįŗ£¨ŃĹłŲńį…ķ»ňĶńņī∑√≤ĽĶę√Ľ”–īÚ∂Įő“£¨∑ī∂Ý»√ő“ĺ™ĽŇ ßīŽ°™°™ňŻ√«“Ľ¬∑īÚŐż◊Ň◊ŖĹÝőńĽĮĻ›īīĪŗ “ Ī£¨“żņī–Ū∂ŗļ√∆śĶńńŅĻ‚°£
°°°°ń«īő£¨”ŽńĹ√Ż∂ÝņīĶńŇů”—ľŻ√ś°™°™ļůņīő“√«≥…ő™ŃňőřĽį≤ĽŐłĶńŇů”—£¨ĺŅĺĻňĶŃň ≤√ī£¨◊ÝŃň∂ŗ≥§ Īľš£¨ő“»ę»Ľľ«≤ĽĶ√Ńň£¨ő©“Ľľ«Ķ√ĶńĺÕ «į—ňŻ√«ňÕ◊Ŗļů£¨∑ĘŌ÷ÕŃĽ∆Ň£∆§÷Ĺ∑‚∆§…Ō°įļŰņľļ”īę°ĪňńłŲ◊÷ŌÚő“…Ńňł◊ŇľĪŇőŇőĶń—Ř…Ů°£ļ‹Ō‘»Ľ£¨ľĪ«–Ķń «ő“∂Ý≤Ľ «ňŁ£¨“Úő™ľĪ«–£¨ő“ŐŠ«įņŽŅ™įžĻę “£¨ĽōĶĹŃňő“ń«łŲ’ŕĪőŃňīįŃĪĶńĽŤįĶĶńňř…Š–°ő›°£ń«ÕŪ£¨ő“≥Ļ“Ļőř√Ŗ£¨ő“ŌŮőŁłĹ‘ŕ“ĽŅťīŇ Į…ŌĶńŐķ–ľ£¨ňś◊ŇīŇ ĮĶń“∆∂ĮőĘőĘ≤Ł∂∂ľ§∂Į≤Ľ“—£¨ŌŰļžĪ Ō¬“ĽĶĹ∂¨ŐžĺÕŃ—ŃňŅŕ◊”ĶńīůĶō£¨“ĽĶĹīļŐžĺÕŌ›ĹÝńŗŨĶń¬Ū≥Ķ£¨÷Ľ”–«ÔŐž≤Ň»»ń÷∆ūņīĶń…Ĺ“į£¨ĽĻ”–ļŕ∆Š∆ŠĶńń•∑Ņ£¨¬©”ÍĶń∑Ř∑Ņ£¨ĽńŃĻĶń≤›∑Ņ»ňľ“£¨ĽĻ”–◊śłł°Ę◊śńł°Ę”–∂Ģ Ś£¨ĽĻ”–‘ŕīůĹ÷…Ō◊‘”…īģ∂ĮĶńÚŖÚ—°Ę¬žÚ∆°Ę–°—ŗ◊”£¨∑÷≤ľ‘ŕ–°≥«Ĺ÷Õ∑ĶńĹū“Ý ◊ őĶÍ°Ę≤ľ◊Į°Ę≤Ť◊Į°Ę≤ ÷Ĺ∆Ő°≠°≠ő“≤Ľ÷™Ķņ «ĪĽ”ő◊Ŗ‘ŕőń◊÷ņÔ◊‘”…◊‘‘ŕĶńŃťĽÍīÚ∂Į£¨ĽĻ «ĪĽŌ‚«∂‘ŕĽń¬ýīůĶō…ŌĶńĻ¬∂ņľŇńĮł–»ĺ£¨ő““Ľĺ≠◊ŖĹÝ»•£¨Ī„‘Ŕ“≤≤Ľń‹◊‘įő°£ń«łŲ“ĻÕŪ£¨ő“ĪĽ…’◊ŇŃň“Ľį„£¨‘ŕī≤…Ō“ĽĽŠ∂ýŇŅŌ¬“ĽĽŠ∂ýŇņ∆ū£¨ő“◊ŖĹÝ»•Ķń£¨Īĺ «ŌŰļžĶńļŰņľļ”–°≥«£¨»īĺűĶ√ń«–°≥«ĺÕ «ő“Ķńľ“ŌÁ–°’Ú£¨ő“ŅīĶĹĶń£¨Īĺ «ŌŰļžĶńÕĮńÍĺįŌů£¨»īĺűĶ√ń«ĺįŌů’ż «ő“ÕĮńÍņÔĶńľ«“š°£Ķŕ∂ĢŐž‘Á…Ō£¨ĶĪő“’Ų◊Ň“ĽňęįĺļžŃňĶńňę—ŘŇņ∆ūņī…Ōįŗ£¨ő“Ķń—Ř«į£¨“—ĺ≠’ĺŃĘ∆ūŃŪ“ĽłŲīŚ◊Į°£ňż◊ý¬š‘ŕĽ∆ļ”ĪĪį∂£¨«įļůĹ÷ŃĹŇŇ≤›∑Ņ£¨ňż«įĪŖ”–ŃĹŐűŌł≥§Ķńļ”Ļ»£¨ļ”Ļ»ŃĹį∂≥§◊Ň∑ŠŇśĶń“į≤›£¨ňżĺÕ «…ķő“—Ýő“ĶńŃ…ńŌŌÁīŚ…Ĺĺ◊◊”°£
°°°°1986ńÍ£¨’‚“ĽńÍ∂‘ő“ Ķ‘ŕŐę÷ō“™Ńň£¨ňŁĶń÷ō“™‘ŕ”ŕ£¨Õ®ĻżŌŰļž£¨ő“ŅīĶĹŃň◊‘ľļĶńīŚ◊Į°£ő“ĶńīŚ◊Į“Ľ÷Ī∂ľ‘ŕ£¨ňŁőĽ”ŕĽ∆ļ£ĪĪį∂£¨»ī≤Ľ ōļ££¨ňŁ Ű”ŕŃ…ńŌ…Ĺ«Ý£¨»ī√Ľ”–…Ĺ£¨ňŁ÷Ľ «“ĽłŲŇŤĶōņÔĶńīŚ◊Į°£ňŁ––’Ģ…ŌŃ• Ű”ŕŃ…ńĢ °◊Įļ”Ōō°™°™◊Įļ”£¨◊Įļ”£¨◊Į◊Į”–ļ”£¨ňý”–Ķńļ”Ļ»∂ľÕ®◊Ňīůļ£°£ő“Ļ ŌÁĶńļ”Ļ»£¨ŃĹį∂≥§¬ķŃň“į≤›£¨ň≥≥§¬ķ“į≤›Ķńļ”Ļ»ŌÚ∂ęńŌ∑ĹŌÚ◊Ŗ£¨≤Ľ≥Ų“Ľ–° ĪĺÕń‹◊ŖĶĹļ£ĪŖ–°’Ú£¨ń«–°’ÚĹ–«ŗ∂—◊”°£‘ŕŌÁŌ¬īŰĶ√ľŇńĮ—ŠĺŽ Ī£¨ĪĽłłńłĻ‹ ÝĶ√ī≠≤ĽĻż∆Ý Ī£¨ĺÕň≥ļ”Ļ»–°ĶņŐ”Õý«ŗ∂—◊”–°’Ú£¨Ň—ńśĶń«ť–ųÕýÕýňś◊Ňļ”Ļ»į∂ĪŖĶń“į≤›“Ľ∆ū“°“∑°£ő“≥ű ľ–ī◊ų£¨ „–īĶńĺÕ «’‚÷÷ľĪ”ŕŐ”ņŽĶńŇ—ńś«ť–ų°£ňš»Ľ‘ŕ’‚÷÷«ť–ų÷–£¨“≤ī•ľįĶĹīŚ◊ĮĶń»ňļÕ ¬£¨“≤√ŤĽśĻżīůĹ÷°ĘÕŃĶō°Ę…Ĺ“į°Ę≤›ī‘£¨Ņ…ő“Ķń«ťł– «—Š∂ŮĶń£¨‘ųļřĶń£¨ő“∂‘īŚ◊Į»ň ¬ĺį÷¬Ķń ť–ī «Ō¬“‚ ∂Ķń£¨≤Ľ◊‘ĺűĶń°£Ňů”—Ō≤Ľ∂°∂–°īį–ű”Í°∑£¨ĽÚ–Ū «ňŻŅīĶĹŃňń«ņÔĪŖŌ¬“‚ ∂Ķń≤Ņ∑÷£¨Ňů”—ĶńŇů”—ňÕņī°∂ļŰņľļ”īę°∑£¨ĽÚ–Ū «ĺűĶ√ő“Ō¬“‚ ∂ ť–īĶńīŚ◊ĮļÕŌŰļžĪ Ō¬ĶńīŚ◊Į”–Ķ„ŌŮ£¨Ņ…ňŻ√«≤Ľ÷™Ķņ£¨ňŻ√«ĽĹ–—Ńňő“∂‘ Ű”ŕ◊‘ľļĶńń«łŲļ”Ļ»īŚ◊ĮĶńł–«ť°™°™ń«Őž‘Á…Ō£¨ĶĪő“¬ķ—Ř∂ľ «ő“Ļ ŌÁĶńīŚ◊Įļ”Ļ»£¨ļ”Ļ»ŃĹį∂∑ŠŇśĶń“į≤›£¨“ĽĻ…÷Ņ»»ĶńŌ™Ńų”ŅĹÝ—ŘĹ«£¨ő““Ľň≤ľš»»ņŠ”ĮŅŰ°£
°°°°—Š∂Ů“≤ «“Úő™įģ£¨‘ųļř“≤ «“Úő™įģ£¨ĺÕŌŮ«ť»ňľšĶńįģľę…ķļř£¨ĺÕŌŮ«◊»ňľšĶńŇ≠∆š≤Ľ’ý°£Ņ… «‘ŕ”ŲĶĹŌŰļž÷ģ«į£¨ő“Ņī≤ĽĶĹ◊‘ľļ∂‘ļ”Ļ»īŚ◊ĮĶń»»įģ°£ő“…ű÷Ń≤Ľ÷™Ķņ£¨ő“‘ŕ–°ňĶņÔ≤Ľ∂ŌĶō ť–īňż£¨ ť–īń«–©¬šļůĶńŃÓő“—ŠĺŽĶń»ňļÕ ¬£¨ŃÓő“∑īł–Ķń…Ł–ůļÕő√”¨£¨’ż“Úő™ő“‘ŕ≤Ľ∂ŌĶōŌÚ◊ŇÕ‚√śĶń∂„Ī‹ļÕŐ”ņŽ÷– ‹ĶĹŃň≥ŚĽųļÕ…ňļ¶£¨ő“ «“Úő™ ‹ĶĹ…ňļ¶≤Ň‘ł“‚ĽōĶĹ–ńĶ◊ĶńīŚ◊Į°£
°°°°…ňļ¶Õ¨—ýņī◊‘”ŕ1986ńÍ£¨’‚“ĽńÍőŚ‘¬£¨ő“ī”“ĽłŲŃ≥≥ĮĽ∆ÕŃĪ≥≥ĮŐžĶńŇ©√Ů“°…Ū“ĽĪš≥…Ńň”Ķ”–≥« –ĽßŅŕĶń≥«ņÔ»ň£¨≥…ŃňŐžŐž‘ŕőńĽĮĶ•őĽ…ŌįŗĶńőńĽĮ»ň£¨Ņ… «“į≤›“Ľ—ý‘ŕ…Ĺ“įņÔ≥§īůĶńő“£¨∂‘įī Ī…ŌŌ¬įŗ£¨∂‘≥Ő–ÚļÕ÷»–Ú”–◊ŇŐž»ĽĶńĶ÷ī•£¨”»∆š ‹ĻżĹŐ”żĶń–°≥«őńĽĮ»ňĶńľŔń£ľŔ Ĺ£¨ő™“ĽľĢ–° ¬∑īłī’ý“ť≤Ľ∂Ō÷ōłīĶńőřŃńĽŠ“ť°£ő“Ī∂ł–—Ļ“÷£¨ő““Úő™—Ļ“÷∂Ý…ķ≥Ų”Ű√∆£¨ő““Úő™”Ű√∆∂Ý…Ůĺ≠ň•»ű£¨Ķ√Ńň—Ō÷ōĶń ß√Ŗ÷Ę°£ľŻĶĹņī∑√ĶńŇů”—£¨∂ŃĶĹ°∂ļŰņľļ”īę°∑£¨’ż « ß√Ŗ◊Óņųļ¶Ķń Ī∆ŕ£¨Õ®ĻżļŰņľļ”–°≥«ŅīĶĹő“Ķńļ”Ļ»īŚ◊Į£¨“Ľ÷Í‘ŕŌÁ“į…Ō“°“°ĽőĽő…ķ≥§Ńň∂Ģ ģ∂ŗńÍĶń“į≤›őř“ž”ŕĽōĶĹń«∆¨◊‘”…ĶńÕŃĶō°£
°°°°ļůņīő“÷™Ķņ£¨ŌŰļž–ī°∂ļŰņľļ”īę°∑£¨ «ňż‘ŕÕ‚√ś ņĹÁ∆£ĪĻ∆ģ≤īĹŁ∂Ģ ģńÍ÷ģļů°£∂Ģ ģńÍņī£¨ňż◊∑«ůłŲ–‘Ĺ‚∑Ň£¨≤Ľ∂ŌĶōī”ŌÁīŚŐ”ņŽ£¨ňżŐ”Õ—łł«◊Ķń◊®÷∆Õ≥÷∆£¨”÷ł– ‹ĶĹń–»®őńĽĮĶń—Ļ∆»£¨ňż°įŐ”Ī‹ń–»®őńĽĮĶń«Į÷∆°Ī£¨”÷‘‚”Ų°į»’Īĺ«÷¬‘’ŖĶńŐķŐ„°Ī£¨◊ÓļůĽľ≤°◊°‘ŕŌ„łŘ°£ĺřīůĶńĻ¬∂ņļÕľŇńĮ∆ň√ś∂Ýņī Ī£¨ňżĶńĪ Ī„ĽōĶĹŃňňš «ľŇńĮĶę»īőřĺ–őř ÝĶńīůĶō£¨ňżĶńŃťĽÍ‘ŕń«ņÔ◊‘”…ĶńŠšŠŗ°£”–—–ĺŅ’ŖňĶ£¨ŌŰļž°į «“ĽłŲ”–◊Ň…ÓŅŐňľŌŽĶń◊ųľ“£¨‘ŕ∂Ő∂Ő ģńÍĶńīī◊ų…ķ—ń÷–£¨–īŌ¬Ńň“ĽįŔÕÚ◊÷Ķń◊ų∆∑£¨ňż”…”◊÷…ĶĹ≥… ž£¨”…Õ∂…ŪĶĹ◊ů“Ūňľ≥ĪĶĹ÷ūĹ•∂ņŃĘ£¨”–“‚ ∂Ķō ŤņŽ÷ųŃų“‚ ∂–őŐ¨Ľį”Ô£¨ňľŌŽĺ≠ņķŃň√ųŌ‘Ķń«įļůŃĹłŲ∑Ę’ĻĹ◊∂ő°Ī°£∂Ýő“»īńĢ‘łŌŗ–Ň£¨ŌŰļžĶń≥… ž£¨ŌŰļžĶń”–“‚ ∂ ŤņŽ÷ųŃų“‚ ∂–őŐ¨Ľį”Ô£¨”–ļůŐžÕ‚≤ŅĽ∑ĺ≥Ķń”įŌž£¨łŁ”–“į≤›“Ľ—ý◊‘”……ķ≥§‘ŕŌÁīŚĶń“Úňō°£‘ŕňżĶńÕĮńÍ£¨ňš“≤”–◊śńłĶńĻ‹ Ý£¨∑‚Ĺ®ņŮĹŐĶń—Ļ∆»£¨Ņ…ŐĻĶīĶńīůĶō°ĘŅ™ņęĶń‘≠“į Ļňż“Ľ÷ĪĪ£”–“ĽŅŇ◊‘”…Ķń–ńŃť°£»ÝŐōňĶ£¨∑≤ «»ň∂ľ”–ňŻĶń◊‘»ĽĶōőĽ£¨’‚łŲ◊‘»ĽĶōőĽĶńłŖ∂»≤Ľ «◊‘◊ūļÕ≤ŇĽ™ňýń‹»∑∂®Ķń£¨∂Ý «∂ýÕĮ Īīķ»∑ŃĘĶń°£»ÝŐōňĶňŻĶń◊‘»ĽĶōőĽ «įÕņŤŃý≤„¬•ń«√īłŖ°£ÕĮńÍ∂‘“ĽŅŇ◊‘”…–ńŃťĶńŇŗ÷≤£¨ ĻŌŰļž∂ŗńÍņī“Ľ÷Ī”–◊Ň«Ś–—Ķńńŕ–ńĪŖĹÁ£¨ĶĪń≥÷÷◊®÷∆ļÕ ÝłŅ°Ę≥Ő–ÚļÕ÷»–Ú…ňļ¶Ńň◊‘”…£¨ňżĶ∂∑ś“Ľ—ý∑śņŻĶń…Ůĺ≠Ī„◊≤ĶĹńńņÔńńņÔĶő—™£¨ňżĶńĪ Ō¬Ī„”–ŃňĪ•¬ķĶńľ§«ť£¨’‚ľ§«ť‘ŕĽōĶĹĻ ŌÁīůĶō Ī£¨Ī„‘Ŕ…ķ≥Ų“ĽłŲņęīůĶń“’ ű ņĹÁ°£
°°°°≥Ų◊Ŗ“Úő™◊∑«ů◊‘”…£¨ĽōĻť“ņ»Ľ“Úő™∂‘◊‘”…Ķń◊∑«ů°£»ň‘ŕ∑‚Ī’”ř√ŃĶńŌÁīŚ£¨ŌÚÕýĶń «Õ‚√śĶńŅ™∑ŇļÕőń√ų£¨ ‚≤Ľ÷™Ņ™∑ŇļÕőń√ų◊‘”–◊‘ľļĶń≥Ő–ÚļÕ÷»–Ú£¨◊‘ľļĶń÷∆∂»ļÕ∑®‘Ú°£’‚÷»–ÚļÕ≥Ő–Ú°Ę÷∆∂»ļÕ∑®‘Ú∂‘…Ū–ńĶń◊‘”… «ŃŪ“Ľ÷÷ ÝłŅļÕŐŰ’Ĺ°£ Ķľ …Ō£¨‘ŕő“1986ńÍ”ŲĶĹŌŰļžĶń ĪļÚ£¨ő“’“ĶĹŃňő“–ńŃťņÔĶń’ś’żľ“‘į£¨ňż‘ŕő“Ķń∂‘√ś”÷‘ŕő“ĶńĪ≥ļů£¨ňż «ő“Ķńľ«“š»ī «“ĽłŲ’ś ĶĶńŌ÷ ĶĶńīŚ◊Į°£ŌÁīŚ”–◊‘ľļĶń÷»–Ú£¨◊‘ľļĶńőńĽĮĹŠĻĻ£¨Ņ…ňż“ĽĶ©Īš≥…ňľńÓļÕĽ≥ŌŽ£¨…żŐŕ‘ŕŌ÷ ĶĶńőń√ų ņĹÁ∂‘į∂£¨ń«ņÔĺÕ≥…Ńň“ĽłŲ◊‘”…ĺę…ŮĶń∆‹ŌĘĶō£¨ĺÕ…ķ≥…≥Ų“ĽłŲņŪŌŽĶń–ťĻĻĶńŅ’ľš°£
°°°°ő“≤Ľ÷™Ķņ£¨ĶĪńÍ«ż≥Ķ∂Ý÷ŃĶńņī∑√’Ŗ£¨ «≤Ľ «–ńŃťĶń◊‘”…‘ŕ–ķŌýĶńŅ™∑Ę«ÝĪ∂ ‹—Ļ“÷£¨≤Ň‘ŕő“őř“‚ ∂–īĶĹĶńīŚ◊ĮņÔ’“ĶĹľńÕ–£Ņ“≤≤Ľ÷™Ķņ£¨ń«őĽňÕő“°∂ļŰņľļ”īę°∑ĶńŇů”—£¨ «≤Ľ «ī”ő“Ķń◊ų∆∑ņÔŃňĹ‚Ńňő“Ķń—Ļ“÷£¨≤Ň”–“‚»√ŌŰļžīÝő“ĽōĶĹ…ŪļůĶńīŚ◊Į£ŅĽÚ’Ŗ£¨ «ňŻ√«ĺűĶ√◊ųő™“ĽłŲ–ī◊ų’Ŗ£¨Īō–Ž÷™Ķņő“ «ň≠£¨ő“ĶńĻ ŌÁ‘ŕńńņÔ£¨≤Ňń‹‘ŕőń◊÷ņÔĹ®ŃĘ∆ū“ĽłŲ◊‘”…Ķń“’ űÕűĻķ£Ņő“≤Ľ÷™Ķņ°£ő“÷Ľ÷™Ķņ£¨’‚ŃĹőĽŇů”—£¨∂ľ≥Ų…ķ”ŕ÷–ĻķĪĪ∑ĹŌÁīŚ£Ľő“÷Ľ÷™Ķņ£¨’‚ŃĹőĽŇů”—£¨ňŻ√«“Ľ¬∑ĪĪ…Ōņī◊Įļ”Ņīő“Ķń ĪļÚ£¨’ż «ňŻ√«“ÚŌŗįģ∂Ý≤Ľń‹£¨‘ŕ–ńĶ◊ņÔŅŗŅŗ’ű‘ķ◊ŇĶń ĪļÚ°£∂ŗńÍ÷ģļůňŻ√«łśňŖő“’‚“Ľ ¬ Ķ£¨ő“≥§ Īľš≥Ńń¨≤Ľ”Ô°£÷Ľ“™ń„–ńņÔ”–“ĽŅŇ◊‘”…Ķń÷÷◊”£¨ń„÷’ĺŅ «“ĽłŲ∆ģ≤ī’Ŗ£¨ń„÷’ĺŅĽŠĪĽŌ÷ ĶĶńņň≥ĪĽųīÚĶ√Õ∑∆∆—™Ńų°£‘≠ņī£¨ĶĪ ĪĶńňŻ√«£¨“≤ļÕŌŰļž“Ľ—ý£¨‘ŕ—į’“◊‘ľļ“į≤›“Ľ—ýĶńÕĮńÍ£¨“‘őŅĹŚĪťŐŚŃŘ…ňĶń–ńŃť°£
°°°°◊ų’Ŗ£ļňÔĽ›∑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