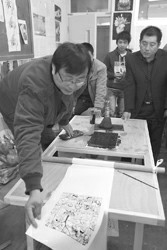°°°°«Ī–ń—–ĺŅ÷–ĻķĶń√Ůľš“’ ű
°°°°∂ľňĶ’ŇŌ‹≤ż’‚»ňļ‹Ļ÷°£∆š Ķ£¨’ŇŌ‹≤żłÝő“ĶńĶŕ“Ľ”°Ōů£¨÷ĽĺűĶ√ňŻ’śĶń≤ĽŌŮłŲĹŐ ŕ£¨ĶŬýŌŮłŲŇ©√ŮĶń°£
°°°°ňŻ≤Ľ–řĪŖ∑ý≤ĽňĶ£¨ňĶ∆ūĽįņī£¨”–Ķń ĪļÚĽĻ∂ę“Ľņ∆Õ∑őų“ĽįŰ◊”Ķń°£ňŻ«į√śňĶĶńĽį£¨ń„ĽĻ√ĽŌŻĽĮÕÍ£¨ňŻĽŠ“≠łÝń„ŃŪÕ‚“ĽłŲĽįŐ‚°£őř¬ŘļÕň≠£¨≤ĽįģĹ≤√ś◊”£¨ňĶĽį÷Īņī÷Ī»•£¨◊‘ľļ‘ű√īŌŽĶń£¨ĺÕ‘ű√ī◊Ų°£łķŃžĶľ“≤»Áīň°£ňŻłŲ–‘“≤«Ņ£¨Īū»ňňĶňŻ°įÍŮ°Ī£¨»żÕ∑¬Ņ∂ľņ≠≤ĽĽōņī°£ňŻĽĻ≤Ľ‘ł“‚ļÕīůĽÔ∂ýĪ≠ņī’Ķ»•Ń≥ļž≤Ī◊”ī÷Ķōļ»ĺ∆£¨ňŻĽŠňĶ£¨°įł…¬Ô£°°Īňý“‘£¨”–≤Ľ…Ŕ»ň≤ĽņŪĹ‚ňŻ°£ňŻłÝ»ňĶńł–ĺű «£¨≤Ľ‘ķ∂—∂ý£¨≤ĽļŌ»ļ∂ý°£
°°°°”–ľĢ ¬łÝő“Ķń”°Ōů◊Ó…Ó°£ňŻ «ńŅ«įŃń≥«īů—ß√ņ ű—ß‘ļńÍŃš◊Óīů°Ę◊ ņķ◊ÓņŌĶńĹŐ ŕ÷ģ“Ľ°£ňŻĶńÕ¨—ß°Ę—ß…ķ£¨“ĽłŲłŲ∂ľ≥…ŃňīůĽ≠ľ“£¨”–Ķń≥…Ńň÷Ý√Żīů—ß√ņ ű—ß‘ļĶń‘ļ≥§£¨”–Ķń‘Úľ”ń√īů°Ę√ņĻķ°Ę»’ĪĺĽÚĪĪĺ©∑Ę’Ļ»•Ńň°£”–≤Ľ…Ŕ»ňĶńĽ≠ń‹¬Úľł«ß‘™“Ľ∆Ĺ≥Ŗ£¨“ĽłŲņŮį›ń‹ÕŅ…Ō ģľł’Ň°£
°°°°Ņ…’ŇŌ‹≤ż√Ľ”–°£∆śĻ÷Ķń «£¨őř¬Ř «Ľķ”Ų£¨ĽĻ «ľľ“’ļÕ√ņ űņŪ¬Ř£¨∂ľī¶‘ŕ…Ō…żÕ®ĶņĶń ĪŅŐ£¨’ŇŌ‹≤ż»ī–ń—™ņī≥ĪĶō‘ŕ◊‘ľļĶń“’ ű∑Ę’Ļ¬∑ĺ∂ļÕ◊ŖŌÚ…Ō£¨ņīŃň“ĽłŲ180∂»Ķńīů◊™Õš£ļ◊Ŗ…ŌŃň«Ī–ń—–ĺŅ÷–ĻķĶńńłŐŚ“’ ű°™°™√Ůľš√ņ űĶńĶņ¬∑°£
°°°°ňŻ÷™Ķņ£¨ňŻĶń’‚łŲĺŮ‘Ů£¨ «ňŻ»ň…ķ◊ÝĪÍĶń◊™’ŘĶ„£ļ“™√īĺÕŌŮĺÝīů≤Ņ∑÷Ľ≠ľ“ń«—ý£¨Ĺ®ŃĘ◊‘ľļĶńĻ§◊ų “°Ę≥…ŃĘĽ≠‘ļ°Ęľ”»Ž °√ņ űľ“–≠ĽŠ£¨»ĽļůŌŽįž∑®‘Ŕľ∑ĹÝ»ęĻķ√ņ űľ“–≠ĽŠ°£”–Ńň’‚–©Ő√∂ÝĽ ÷ģĶń◊ Īĺ£¨ĺÕŅ…“‘≥Ų»•°į◊Ŗ—®°Ī£¨«įļŰļů”Ķ£¨◊Ŗ…Ō“ĽŐű“‘¬ŰĽ≠ő™…ķĶń◊®“ĶĽ≠ľ“Ķń¬∑£Ľ“™√īĺÕ“Ľ…ķ«Ś∆∂£¨ļÕńÍĽ≠°™°™’‚–©ĪĽ≤Ľ…Ŕ»ň≥∆◊ų≤ĽĶ«°įīů—Ň÷ģŐ√°ĪĶńÕś“‚∂ýő™őť°£ī”īň£¨őř√ŻőřņŻ£¨∑ÁņÔņī°Ę”ÍņÔ»•£¨“Ľ…ŪńŗįÕ“Ľ…ŪļĻňģĶō‘ŕŌÁľšĻŲņīĻŲ»•°£
°°°°’ŇŌ‹≤ż—°‘ŮŃňļů’Ŗ°£
°°°°ő“ő ĻżňŻ£¨ő™ ≤√ī—°‘ŮĶń «ļů’Ŗ£ŅňŻň∆ļű≤ĽľŔŅľ¬«ĶōĽōīūő“£ļ°įő“≤Ľ»•ł…£¨“≤ĽŠ”–»ň»•ł…°£÷–ĻķĶń—ß’Ŗ◊‹Ļť”–»ň»•◊Ų’‚ľĢ ¬∂ý£¨ő“÷Ľ «‘ŕ√Ľ”–»ň◊ŲĶń«ťŅŲŌ¬Ō»◊ŖŃň“Ľ≤Ĺ°£°Ī
°°°°‘ŕ’‚łŲ»ň…ķĶń ģ◊÷¬∑Ņŕ…Ō£¨ňŻ◊ŖĪťŃňŃń≥«Ō¬ŌĹĶńŃŔ«Ś°ĘĻŕŌō°Ę›∑Ōō°Ę—ŰĻ»°Ę∂ęįĘ°Ę‹›∆Ĺ°ĘłŖŐ∆°Ę∂ę≤żłģ«ÝļÕ”…Ńń≥«īķĻ‹Ķń °ŌĹ –ŃŔ«Ś –ĶńŌÁīŚ°Ę≥«’Ú°£÷ģļů£¨ňŻĶń◊„ľ£”÷…žŌÚŃň…Ĺ∂ę°Ęļ”ńŌ°Ęļ”ĪĪ»ż °ĹĽĹÁĶń‘ňļ”ŃĹį∂£¨ĹÝ––√Ůň◊őńĽĮ°Ę√Ů◊Ś“’ űŐÔ“įŅľ≤ž°Ę ’ľĮ°Ę’ŻņŪ°£√ŮľšńĺįśńÍĽ≠°Ęńŗň‹°ĘľŰ÷Ĺ°Ę√śň‹°ĘńĻ÷ĺ°Ęņľ”°°Ę«ŗĽ®°Ęļý¬ę°ĘŇ©īŚ∆∆ĺ…ľ“ĺŖ°Ę¬ŪĪř◊”°Ę…ŁŅŕŐ◊°Ę Įń•°Ę¬Ū‘ķ°Ę Į∂’°Ę√ļ”ÕĶ∆°ĘĪ‚Ķ£°ĘńĺÕ∆≥Ķ°Ęĺ…√ŇįŚ£¨∂ľ≥…ŃňňŻ…śŃ‘Ķń∂‘Ōů°£ňŻ“ĽľĢ“ĽľĢĶōį—ňŁ√«ī”Ň©īŚņŌįŔ–’ľ“ņÔ£¨įŠĹÝŃňŃń≥«īů—ߣ¨≥Ň∆ūŃňŌ÷‘ŕĶńŃń≥«īů—ß√Ůň◊—–ĺŅňý°£
°°°°’ŇŌ‹≤ż√Ņ ’ľĮĶĹ“ĽľĢ√Ůň◊“’ ű∆∑£¨∂ľĽŠ”–“Ľ∂ő∂Į»ňĶńĻ ¬°£
°°°°1986ńÍ£¨īļĹŕł’Ļż°£”–ņŌŌÁłśňŖ’ŇŌ‹≤ż£¨ňĶ›∑Ōō›∑Õ§’ÚĶ•√ŪīŚ–¬∑ĘŌ÷Ńň≤Ľ…ŔńÍĽ≠£¨»√’ŇŌ‹≤ż»•ŅīŅī°£’ŇŌ‹≤ż”–łŲ√ę≤°£¨≤ĽĻ‹‘ŕ ≤√ī ĪļÚ£¨“ĽŐŠĶĹńÍĽ≠ĽÚļÕńÍĽ≠”–ĻōĶń ¬∂ý£¨ňŻĽŠŐűľĢ∑ī…šĶōŐÝĹę∆ūņī£ļ°į‘ŕńń£Ņ°Īňśļů£¨◊ľĽŠÕ¬≥ŲĻ“‘ŕ◊žĪŖĶńń«ľłłŲ◊÷£ļ°į◊Ŗ£°ŅīŅī»•°£°Ī
°°°°įģ»ň‘ŕĽķĻō…Ōįŗ£¨”◊∂ý‘įĽĻ√Ľ”–Ņ™—ߣ¨őŚňÍĶńļĘ◊”√ĽĶō∑Ĺ∑Ň°£’ŇŌ‹≤żŅ…≤ĽĻ‹’‚–©£¨ňŻ»√ļĘ◊”◊Ý‘ŕ◊‘––≥ĶĶńīůŃļ…Ō£¨”≤ «∂•◊Ňļģ∑ÁīÝ◊ŇļĘ◊”ņīĽō∆ÔŃň70ĻęņÔĶń¬∑°£ī”Ńń≥«ĶĹ›∑Ōō£¨ńńŌŮŌ÷‘ŕ“Ľ—ý∂ľ «ľł≥ĶĶņĶńłŖĶ»ľ∂Ļę¬∑°£ń« Ī£¨»ę «ÕѬ∑°£∆Ż≥Ķ“ĽĻż£¨Ľ“ŐžĽ“Ķō£¨Ń¨«į√śĶń¬∑∂ľĪś≤Ľ«Ś°£‘ŔÕýīŚņÔ∆Ô£¨—©ňģĹŃ◊Ňņ√ńŗĶō£¨“Ľ∆¨ńŗŇĘ°£Ķ»ĶĹŃňīŚņÔ£¨ļĘ◊”ĶńŃĹŐűÕ»¬ťĶ√≤Ľń‹Ō¬≥Ķ°£ļ”ĶÍ’ÚőųĻýīŚ «őŇ√Ż‘∂ĹŁĶń°įńŗň‹īŚ°Ī£¨’ŇŌ‹≤żŌŽ£¨ņī“ĽŐň≤Ľ»›“◊£¨ňŻ”÷Ńž◊ŇļĘ◊”…”īÝ◊ŇŇ‹ŃňŐňőųĻý£¨ĹÝīŚ∂ýŅīńŗ∆–»Ý»•Ńň°£
°°°°ī”1990-1996ńÍ£¨’ŇŌ‹≤ż”√Ńň6ńÍĶń Īľš£¨‘ŕŃń≥«Ň©īŚ◊‚Ńňľš–°ő›£¨į—◊‘ľļĻō∆ūņī£¨∆ĺĹŤ◊Ň∂‘īęÕ≥őńĽĮĶń»»įģ£¨ī”“ĽłŲ ’≤ōľ“ļÕ—ß’ŖĶńĹ«∂»≥Ų∑Ę£¨‘ŕ√Ůľš ’ľĮŃňīůŃŅņī◊‘≤ĽÕ¨Ķō«Ý°Ę…ů√ņ–őŐ¨łų“žĶńńĺįś”°ňĘ÷ŬŽńÍĽ≠£¨÷ō–¬Õ≥“Ľ≥ŖīÁ∆ūłŚ°Ę∑Ňīů°ĘĽś÷∆£¨ÕÍ≥…Ńň”…”ŕńÍīķĺ√‘∂ĽÚĪ£īś≤ĽĶĪňý‘ž≥…Ķńňūļń°Ęń£ļżĶ»ő Ő‚°£‘Ŕīī◊ųŃňľ»Ī£≥÷ńĺįśńÍĽ≠Ķń‘≠”–∑ÁłŮ£¨”÷≤Ľ ß»•‘≠ĪĺĶń…ę≤ ĻōŌĶļÕņķ ∑ł–£¨«“őŁ ’ŃňŌ÷īķ“’ űĪŪŌ÷ľľ∑®ĶńńÍĽ≠–¬◊ų°£ňŻĽ≠Ńň120∑ý£¨Ľ≠Ķ√ļ‹ņŘ°£
°°°°ňŻňĶ£¨ňŻ“Ľ’ŇĽ≠∂ý£¨Ķ√Ľ≠įŽłŲ‘¬°£’‚÷–ľš≤Ľ÷™ĶņňļŃň∂ŗ…Ŕ’Ň°£”–ĶńŇů”—»įňŻ£¨ń„’‚ «ļőŅŗńŇ£Ņ”–’‚Ļ§∑ÚĽ≠Ķ„∂ýĽ®ńŮ°ĘĽ≠Ķ„∂ý…Ĺňģ°ĘĽ≠Ķ„∂ý»ňőÔ£¨őř¬Ř «Ļ§Ī £¨ĽĻ «–ī“‚£¨ń„≤Ľ «≤Ľ––°£ňŻ“ĽĺšĽįŐż≤ĽĹÝ°£÷ĪĶĹ2009ńÍ9‘¬£¨ňŻĶń’‚Īĺ°∂÷–Ļķ√Ůň◊įŔÕľ°∑≤ŇĶ√“‘≥Ųįś°£
°°°°ňŻňÕŃň“ĽĪĺ°∂÷–Ļķ√Ůň◊įŔÕľ°∑łÝő“°£ő“∑≠Īť»ę ť£¨∑ĘŌ÷≥żŃň◊ų∆∑°Ę◊ų∆∑ľÚĹťļÕ’ŇĶņ“ĽŌ»…ķ°ĘÕű ųīŚŌ»…ķ°Ę’ŇŠ∑ńÍŌ»…ķ°ĘÔŮĺīőńŌ»…ķĶńňń∑ýŐ‚ī Õ‚£¨ņÔĪŖ√Ľ”–ňŻ’ŇŌ‹≤ż“ĽłŲ◊÷∂ý£¨≥ż∑‚√śÕ‚£¨łŁ’“≤ĽĶĹňŻ’ŇŌ‹≤żĶńīů√Ż°£
°°°°ń„ňĶňŻ’‚ «‘≠īī◊ų£¨ĽĻ «‘Ŕīī◊ų£Ņ»√»ňŇ™≤Ľ«Ś°£
°°°°≥Ķ‘ŕŃń≥«īů—ßĶńņŌľ“ Űňř…Š«Ý∂ę‘∑‘į9ļҬ•Õ£ŃňŌ¬ņī°£’ŇŌ‹≤ż≤Ľļ√“‚ňľĶōňĶ£ļ°į≤‹ņŌ ¶£¨ Ķ‘ŕ «Īß«ł£¨ő“◊°‘ŕ6¬•£¨√Ľ”–ĶÁŐ›£¨Ķ√»√ńķŇņ¬•Ő›Ńň°£°Ī
°°°°√Ůľš∑ĘĺÚ°į÷–Ļķ√Ň…ŮĽ≠÷ģ◊Ó°Ī
°°°°łķ◊Ň’ŇŌ‹≤ż“ĽŅŕ∆ÝŇņĶĹŃý¬•Ķń ĪļÚ£¨ő““— «…Ō∆Ý≤ĽĹ”Ō¬∆ÝŃň°£ņīŅ™√ŇĶń «ňŻĶń∑Ú»ň°™°™–ĽņÓĽ™£¨“ĽőĽł’ł’ī”Ńń≥«ŐŚőĮÕň–›ĶńĽķĻōł…≤Ņ°£
°°°°’ŇŌ‹≤żĺ∂÷Īį—ő“ŃžĹÝňŻĶń ť∑ŅľśĽ≠ “°£
°°°°įł◊ņ…Ō£¨Ń„∆ŖįňňťĶō∂—¬ķŃňłų÷÷∂ęőų£ļĪ ľ«Īĺ°Ę√Ż∆¨°ĘĽ≠Ńň∂ŗ“ĽįŽĶńĽ≠÷Ĺ°Ę≥®◊Ňł«∂ýĶń”°ńŗ£¨√ęĪ “≤ «∂ę“Ľ÷¶őų“Ľ÷¶£¨ ťřŻŃň“Ľ≤„”÷“Ľ≤„£¨ĽĻľ–◊Ňłų÷÷—’…ęĶń÷ĹŐű£Ľ÷ųő‘ “£¨≥żŃň“Ľ’Ňňę»ňī≤Õ‚£¨“Ľ»ň∂ŗłŖĶńńÍĽ≠£¨“ĽįŁ“ĽįŁŌŮ–°…Ĺň∆Ķń∂—¬ķŃň’Ż’Ż“Ľ«Ĺ£¨“ĽĶĢ“ĽĶĢĶō”√ň‹ŃŌīŁ◊į◊Ň°£ł®ő‘ “£¨ňš «∂ý◊”◊°£¨Ķę»ÁĹŮ£¨∂ý◊”’һّŕĪĪĺ©£¨ĹÝŃň÷–Ļķ»ň√Ůīů—ߣ¨łķ◊ĮŅ◊’—Ō»…ķ∂Ń≤©£¨—ßĶń «»ňņŗ“’ ű—ß°£Ň™ĶĹ◊Óļů£¨łł◊”Ń©ĽĻ «ł„ĶĹ“ĽŅť∂ý»•Ńň°£∂ý◊”ľŔ∆ŕ≤ŇĽōņī£¨’‚ľšő›◊”“≤ĺÕĪš≥…Ńň’ŇŌ‹≤żĶńŃň°£ ť∑ŅľśĽ≠ “ļÕ—ŰŐ®ŌŗѨ£¨ĪĪ∑ĹĶń—ŰŐ®Õ¶īů£¨Őý◊ŇŃĹŃÔ∂ý«Ĺ£¨¬Ž◊Ňīůīů–°–° ģ∂ŗłŲ÷ĹŌš£¨÷–ľšļ‹ń—‘Ŕ”–≤Ś◊„÷ģĶō£¨÷ĹŌšņÔ√ś“≤∂ľ «’ŇŌ‹≤ż ’ľĮĶĹĶń°į∂ę≤żłģ°ĪĶń∂ęőų°£
°°°°°į’‚ņÔ√ś∂ľ «ļ√∂ęőų£°°ĪňŻį—“ĽįŁńÍĽ≠łŖłŖĶōĺŔĻżÕ∑∂•£¨Ņš“ę◊Ň°£
°°°°°į»ę «ňŻĶń£¨ő“Ѩ≤ŚĹŇĶńĶō∑Ĺ∂ľ√Ľ”–°£ĽĻ≤Ľ»√Īū»ň∂Į°£ń„łÝňŻ ’ įį…£¨ňŻĽĻ≤ĽłŖ–ň°£°Ī–ĽņÓĽ™ĶĪ◊Ňő“Ķń√ś∂ý£¨ ż¬š◊Ň°£
°°°°≤ĽĻż£¨ňżňĶ£¨ňż“≤ŌįĻŖŃň°£°įň≠»√ňŻŌ≤Ľ∂’‚–©Õś“‚∂ýńŇ£°°Ī
°°°°ő“į—ńŅĻ‚“∆ŌÚ’ŇŌ‹≤ż°£ő“∑ĘŌ÷£¨’‚ ĪĶń’ŇŌ‹≤ż£¨Ń≥…Ō∑ļ◊Ҭķ“‚ĽÚ’ŖňĶ «Ķ√“‚Ķń–¶»›°£
°°°°Ńń≥«£¨√ų≥Į≥∆°į∂ę≤żłģ°Ī°£∂ę≤żłģīęÕ≥Ķń√ŮľšńĺįśĽ≠ «ő“Ļķ√Ůľš“’ űĪ¶Ņ‚÷–“ĽŅŇŤ≠Ť≤Ķń√ų÷ť£¨“≤ «Ō÷īķ“’ űīī◊ųĶńĪ¶Ļů≤∆łĽ°£’‚ņÔĶńńĺįśńÍĽ≠£¨‘ŕ√ų«Ś Ī∆ŕĺÕ–ő≥…Ńň◊‘ľļĶń°įŃžĶō°ĪļÕ∑Ę––ÕݬÁ£¨ «īů÷ŕĻę»ŌĶńňĘ”°√ŮľšįśĽ≠Ķń÷––ń÷ģ“Ľ°£
°°°°ňŻłśňŖő“£¨÷–Ļķ√ŮľšńĺįśĽ≠£¨Ő∆“‘«įőī∑ĘŌ÷”–őńŌ◊ľ«‘ō£¨ňőīķŅ™ ľŃų––∂ņ∑ýįśĽ≠£¨ĶĪ ĪĹ–°į÷ĹĽ≠°Ī£¨√ų≥Įłń≥∆°įĽ≠Őý°Ī£¨«Ś≥ű”–ĶńĶō∑ĹĹ–◊Ų°įőņĽ≠°Ī£¨ĽĻ”–ĶńĶō∑Ĺ≥∆◊Ų°įĽ≠’Ň°Ī°£ĺ›ňŻŅľ÷§£¨°įńÍĽ≠°Ī“Ľī £¨‘Ú≥ŲŌ÷”ŕ«ŚĶņĻ‚∂Ģ ģĺŇńÍ£¨ľī1849ńÍ°£
°°°°‘ŕ»ęĻķńĺįś”°ňĘĶń√Ň…ŮĽ≠÷–£¨∑ÁłŮłų◊‘”–∆šŐōĶ„£¨”–Ķń”°ňĘ∑«≥£ĺę√ņ£¨”–Ķń «“‘ő»÷ōĶń‘ž–ÕľŻ≥§°£∂Ýő©∂ņ∂ę≤żłģ√Ň…ŮĽ≠°∂«ō«Ū°∑£¨‘ž–Õ…ķ∂Į°Ę”°ňĘľÚĹŗ£¨«°ĶĹļ√ī¶Ķō ųŃĘŃň√Ůľš“’ űĶń∑ÁłŮ£¨“ÚīňĪĽ“’ űĹÁ≥∆ő™÷–Ļķ√Ň…ŮĽ≠÷ģ◊Ó°£ňőīķ√Ůľš–ň ĘÕĮ◊”ÕřÕřŐ‚≤ń£¨°∂ÕĮ◊”Ľ®ņļ°∑’‚∑ýńÍĽ≠£¨ňš»Ľő“√«…–őřĺŖŐŚőńŌ◊Ņľ÷§∆š‘ī◊‘ňőīķ£¨Ķę «£¨’‚∑ý◊ų∆∑ňýłÝ”Ťő“√«Ķńń«÷÷ĻŇ∑ÁĻŇ‘Ō£¨“—ĺ≠ŌÚő“√«īęĶ›ŃňĻŇņŌ“’ űĶń∑ŻļŇ–ŇŌĘ°£≤Ę«“£¨‘ŕňý”–∆šňŻĶō«ÝĶń÷–ĻķńÍĽ≠÷–£¨√Ľ”–Õ¨—ýŐ‚≤ńĶń◊ų∆∑£¨’‚”÷ «∂ę≤żłģńÍĽ≠∆š√÷◊„’šĻů÷ģī¶°£
°°°°«Ś≥Į«¨¬°ńÍľššÓ‘ň∂¶ Ę£¨∂ę≤żłģ…ýÕŻĺÁ‘Ų£¨ĪĽ”Ģő™°įÕžšÓ÷ģ— ļŪ£¨Őžłģ÷ģ∑őł≠°Ī°£”…šÓ‘ňīÝņīĶń–ň¬° Ę ņ—”÷ŃĻę‘™1854ńÍ£¨«įļů≥§īÔ400”ŗńÍ°£
°°°°°į∂ę≤żłģīęÕ≥√ŮľšńĺįśĽ≠°ĪĺÕ «‘ŕ’‚Ņťő÷ÕŃ…Ō”¶‘ň∂Ý…ķ°£ī”∂ę≤żłģ“ŇŃŰŌ¬ņīĶń°∂ÕĮ◊”Ľ®ņļ°∑ńÍĽ≠Ņī£¨’‚÷÷įśĽ≠ «ī”ňőīķ∂ņ∑ýįśĽ≠√ņŇģÕřÕř∑Ę’Ļ∂ÝņīĶń°£Ļę‘™1127ńÍ£¨ĹūĪÝĻ•∆∆„ÍŃļ£¨“Ľ–©ĶŮįśĻ§Ĺ≥ĪĽ¬įÕý∆Ĺ—Ű(ĹŮ…ĹőųŃŔ∑ŕ)£¨ Ļ’‚łŲĶō«Ý≥…ő™ĶŮįś”°ňĘĶń“ĽłŲ÷––ń°£ĶĹ«Śń©£¨∂ę≤żłģ≤ķ…ķŃň°įőŚł£Ōť°ĪĶ»20”ŗľ“ĹŌīůĶńĶÍ√ś°£√ŮĻķ Ī∆ŕ£¨∂ę≤żłģńĺįśńÍĽ≠īÔĶĹ∂¶ Ę Ī∆ŕ°£ĹŁīķ”…”ŕšÓ‘ňĶń∑Ō÷Ļ£¨‘ňļ”∂ŌŃų£¨ĹÚ∆÷°Ęĺ©ļļŐķ¬∑Ķń–ň–ř£¨ĺ©ļľīů‘ňļ”łÝ”Ť¬≥őųĪĪĶńĶōņŻ»’Ĺ• ĹőĘ£¨∑ŠłĽ∂ŗ≤ Ķń∂ę≤żłģńÍĽ≠“≤ ß»•ŃňÕý»’ĶńĽ‘ĽÕ°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