Š│═Ō▓ž░¹╝─╚╦└ķŽ┬ ╣╩═┴─č╗žŽń│Ņ│Żį┌
 ▓╬ėļ╗źČ»(0)
▓╬ėļ╗źČ»(0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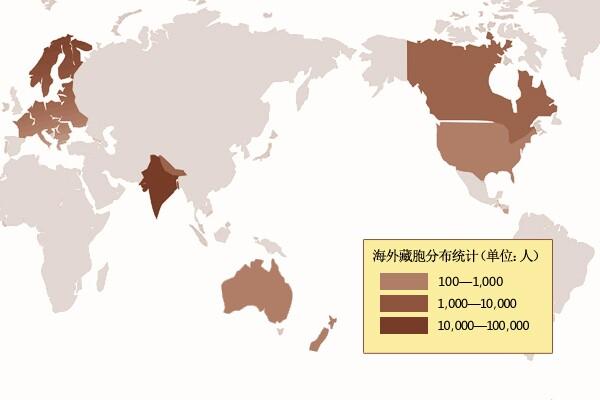
Š│═Ō▓ž░¹Ą─Ęų▓╝═╝Ż║Š▌ųą╣·╣·Ū╚░ņ╩²Š▌Žį╩ŠŻ¼─┐Ū░Š│═Ō▓ž░¹╩²┴┐į╝╬¬20═“╚╦Ż¼│²╚źČ©ŠėėĪČ╚Ą─Į³11═“╚╦Ż¼╝░╔·╗Ņį┌─ß▓┤Č¹Ą─3═“ČÓ╚╦Ż¼Ųõ╦¹ų„ę¬Ęų▓╝į┌31Ė÷╣·╝ę║═ĄžŪ°Ż¼ęį├└╣·Īó╝ė─├┤¾Īó╚╩┐Īóėó╣·Īó░─┤¾└¹čŪĪóą┬╬„└╝╬¬ų„ĪŻŻ©ųŲū„Ż║└Ņč▐ ┴§┼¶Ż®
ĪĪĪĪĪ░╬ęŽųį┌▓╗ų¬Ą└Ė╔╩▓├┤║├ĪŻ┐┤ĄĮ╬ęĄ─Ųõ╦¹═¼░¹į┌ėĪČ╚ę▓Č╝╣²ū┼╬▐Ė∙╬▐┬õĄ──č├±╔·╗ŅŻ¼╬ę▓┼ų¬Ą└╬ęĄ─│÷╠ė╩Ūę╗Ė÷Š°ČįĄ─┤Ē╬¾ĪŻŽųį┌╬ęų╗Žļ╗ž╝ęŻ¼╗žĄĮ╬ęĄ─╣╩Žń└Ł╚°ĪŻ─ŃĖµ╦▀╬ęŻ¼╬ę─▄╗ž╚ź┬Ż┐Ī▒
ĪĪĪĪĪ¬Ī¬ę╗Ė÷ĮąŲĮ┤ļĄ─ųą─Ļ╚╦2012─Ļ10į┬į┌ą┬Ą┬└’ČįĪČ╗ĘŪ“╩▒▒©ĪĘĄ─╝Ūš▀╦Ą
ĪĪĪĪŠ▌ųą╣·╣·Ū╚░ņ╩²Š▌Žį╩ŠŻ¼─┐Ū░Š│═Ō▓ž░¹╩²┴┐į╝╬¬20═“╚╦Ż¼│²╚źČ©ŠėėĪČ╚Ą─Į³11═“╚╦Ż¼╝░╔·╗Ņį┌─ß▓┤Č¹Ą─3═“ČÓ╚╦Ż¼Ųõ╦¹ų„ę¬Ęų▓╝į┌31Ė÷╣·╝ę║═ĄžŪ°ĪŻį┌Š│═Ō▓ž░¹ųąŻ¼Š°┤¾ČÓ╩²╩Ūį┌1959─ĻĖ·╦µ╩«╦─╩└┤’└Ą└«┬’┤ė╬„▓ž┼č╠ėĄĮėĪČ╚Īó─ß▓┤Č¹Īó▓╗ĄżĄ╚ĄžŻ¼│╔╬¬Ī░┴„═÷─č├±Ī▒ĪŻšŌą®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ę▓├╗ėąŽļĄĮ╦¹├ŪĄ─┴„═÷╔·╗Ņę╗╗╬Š═╩Ū░ļĖ÷╩└╝═ĪŻ─Ū├┤│ųėą─č├±╔ĒĘ▌Īó┤”ė┌Ę©┬╔▒▀įĄĄž╬╗Ą─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╔·╗ŅĄ├į§č∙Ż┐
ĪĪĪĪ┤’└╝╚°└ŁŻ║╬▐┤”╗░ŲÓ┴╣
ĪĪĪĪ┤’└╝╚°└ŁŻ¼╩Ū╩«╦─╩└┤’└Ą└«┬’Ą─įó╦∙ęį╝░╦∙╬ĮĪ░╬„▓ž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╦∙į┌ĄžĪŻ╦³╬╗ė┌ėĪČ╚▒▒▓┐Ž▓┬Ē┘╔Č¹░ŅĄ─╬„▒▒╔ĮŪ°Ż¼Ęų╔ŽŽ┬┴Į▓┐ĘųĪŻŽ┬┤’└╝╚°└Ł║Ż░╬1250├ūŻ¼╗∙▒Š╩ŪĄ▒ĄžėĪČ╚╚╦ŠėūĪĪŻ║Ż░╬į╝1800├ūĄ─╔Ž┤’└╝╚°└Ł▒╗│Ų╬¬┬¾┐╦└═Ą┬Ż¼ęŌ╬¬Ī░ąĪ└Ł╚°Ī▒Ż¼╚╦╩²ų╗ėą8000ČÓ╚╦Ż¼╣µ─Żų╗ŽÓĄ▒ė┌ę╗Ė÷Žńš“Ż¼╬¬▓žūÕ╚╦Š█ŠėŪ°ĪŻ
ĪĪĪĪ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ų╗─▄─├─č├±╔ĒĘ▌Ż¼▓╗─▄╝ė╚ļĄ▒Ąž╣·╝«ĪŻ╦õ╚╗ėą▓╗╔┘╚╦╩Ūį┌ėĪČ╚│÷╔·Ż¼Ą½╚┤ė└įČ╩Ū─č├±╔ĒĘ▌Ż¼ę“╬¬╩Ū▒╗╩š╚▌Ą─Ī░┐═╚╦Ī▒Ż¼╦∙ęį▓╗─▄ė└Š├ąįĄž╣║┬“║═ėĄėą═┴Ąž╝░Ę┐▓·Ż¼ų╗─▄ūŌĮĶĪŻ
ĪĪĪĪ2014─Ļ6į┬12╚š├└╣·╬„▓žĄńčČ═°┐»Ęó┴╦į┌├└╣·Ą▒╣²▒°Ą─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├ū└ŁĄ─ĪČ┤’└╝╚°└ŁČį▓ž╚╦░▓╚½┬Ż┐ĪĘę╗╬─ĪŻ╬─š┬ųĖ│÷┤’└╝╚°└ŁĄ▒ĄžėĪČ╚▓┐┬õČį▓žūÕ╚╦╩Ą╩®Ų╚║”║═Ų█č╣Ż¼│ųėą─č├±╔ĒĘ▌Ą─▓žūÕ╚╦╔·╗Ņ▓╗┐░ę╗╗„ĪŻ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▒╗▒ŲĄĮ┴╦š■ų╬ŠŁ╝├Ą─▒▀įĄŻ¼╔·╗Ņū┤┐÷└¦ŠĮŻ¼═¼╩▒╗╣įŌ╩▄├±ūÕŲń╩ėĪó├±ūÕų„ęÕ║═─░╔·╚╦Ęóą╣Ą─│║▐ĪŻ
ĪĪĪĪĪ░╚ź─ĻŻ¼┤’└╝╚°└Łę╗├¹30ČÓ╦ĻĄ─▓ž╚╦─ąūėį┌ę╗│Īš∙ų┤ųą▒╗Ą▒Ąž6├¹Õ╚ĄŽ╚╦Ż©╔·╗Ņį┌┤’└╝╚°└ŁĄ─ėĪČ╚▓┐ūÕų«ę╗Ż®┤ė3▓Ń┬źĖ▀Ą─Į©ų■╚ėŽ┬Ż¼ų«║¾Ė▀╬╗Įž╠▒Ż¼Č°į¬ąū▓ó╬┤╩▄ĄĮĘ©┬╔ųŲ▓├ĪŻę╗├¹▓ž╚╦ĖŠ┼«ę╣╝õ┤Ņ│╦╣½╣▓Ų¹│ĄŻ¼į┌┤’└╝╚°└ŁĖĮĮ³Ž┬│ĄįŌŪ┐▒®║¾▒╗Õ╚ĄŽ╦Š╗·║═╩█Ų▒į▒ȬŲ·┬Ę▒▀ĪŻČÓ├¹▓ž╚╦─ß╣├ę╣╝õ│╦│÷ūŌ│ĄĘĄ╗ž─ß╣├╦┬═ŠųąįŌÕ╚ĄŽ╦Š╗·╔¦╚┼Ū┐▒®ĪŻ╝Ė├¹▓ž╚╦ę“▒¦į╣į┌Ų¹│ĄšŠĄ─╬ń▓═▒╗ČÓ╩šĘčČ°▒╗╚Ł┤“Į┼╠▀ĪŻ╬ęūį╝║ę▓ę“╩į═╝▒Ż╗żę╗├¹▒╗Õ╚ĄŽ╚╦═Ų▐·Ą─▓ž╚╦Č∙═»▒╗╚║┼╣ĪŻĪ▒Ż©š¬ūį├ū└ŁĪČ┤’└╝╚°└ŁČį▓ž╚╦░▓╚½┬Ż┐ĪĘŻ®
ĪĪĪĪĪ░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Ą─Ė»░▄ėļĄ└Ą┬┬┘╔ź
ĪĪĪĪėļŲš═©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└¦┐ÓĄ─╔·╗ŅŽÓ▒╚Ż¼ę▓Ą─╚Ęėąę╗╚║╚╦╣²Ą├▒╚ĮŽū╠╚¾Ī¬Ī¬╦∙╬ĮĄ─Ī░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Ī░╣┘į▒Ī▒ĪŻ╦¹├Ū┐┐╦░╩š║═╣·╝╩į«ų·Ī░Ęó▓Ųų┬Ė╗Ī▒Ż¼▓óŪę┤¾ČÓ│ųėą├└╣·Īó╝ė─├┤¾┬╠┐©ĪŻ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ČįšŌ░’Ī░╣┘į▒Ī▒Ą─Ė»░▄įńęč╝¹╣ų▓╗╣ųĪŻ╦¹├ŪŲ°Ę▀Ąž╦ĄŻ¼į«ų·ėąę╗░ļęį╔Ž▒╗šŌą®ų¹│µė├ė┌│į║╚µ╬Č─┴╦Ż¼Č°šµš²ąĶę¬░’ų·Ą─╚╦╚┤Ęų▓╗ĄĮČÓ╔┘į«ų·ĪŻ├ū└Łį┌Ųõ╬─š┬ųąę▓║┴▓╗┐═Ų°Ąžų╩╬╩Ż║Ī░┴„═÷š■Ė«═Ę─┐├Ū┐╔ęį▓╗Ž¦ę╗Ūą┤·╝█Š┘╝ęŪ©Šė├└╣·▓©╩┐Č┘Ż¼╗“╩Ūį┌ėĪČ╚ėĄėąę╗╠ū┤¾Ę┐ūėŻ¼╚┤į§─▄╬▐╩ė▓╗╩ČūųĄ─ŪŅ┐Ó▓ž╚╦Ą─└¦Š│─žŻ┐Ī▒
ĪĪĪĪėļ┤╦═¼╩▒Ż¼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Ą─└¦ŠĮę▓Ė°┴╦Ī░▓žČ└Ī▒Ą╚Ęų┴č╩Ų┴”║═Ųõ╦¹▒ėąė├ą─Ą─Ę┤╗¬ĪóČ¾╗¬╝»═┼ųŲįņ┴╦┐╔└¹ė├Ą─Ų§╗·║═ŲÕūėĪŻ
ĪĪĪĪŠ▌ųą╣·ūżėĪČ╚┤¾╩╣╣▌Ą─ę╗╬╗Ū░═ŌĮ╗╣┘═Ė┬ČŻ¼šµš²ų¦│ųĪ░▓žČ└Ī▒Ą─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╬¬╩²║▄╔┘Ż¼╦¹├Ūų«╦∙ęįŠŁ│ŻųŲįņ╩┬Č╦Ż¼š²╩Ū╩▄ĄĮĪ░╬„▓ž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ęį╝░Ī░▓žŪÓ╗ßĪ▒Ą╚Ė„ųųĪ░▓žČ└Ī▒ūķų»Ą─Į╠╦¶║══■ą▓ĪŻ═¼╩▒Ż¼Ī░Ī«▓žČ└Ī»╗ŅČ»ę╗ŠŁŲž╣ŌŻ¼─ų╩┬ĘųūėĖ³╚▌ęū╔ĻŪļ├└╣·Ū®ųżĪŻšŌč∙ę╗└┤Ż¼╔§ų┴ėą▓ž╚╦Į½ūķų»Ī«▓žČ└Ī»Ęų┴č╗ŅČ»ū„╬¬─▒╔·Ą─ų░ęĄĪ▒ĪŻ
ĪĪĪĪ╚╗Č°ČÓ─Ļ└┤Ż¼Ęų┴č╗ŅČ»├╗ėą╚ĪĄ├įżŲ┌ą¦╣¹ę▓įĮ└┤įĮ▓╗Ą├╚╦ą─ĪŻ2012─ĻĪ░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ėų▓▀╗«╔┐Č»ūķų»ūįĘ┘ū„╬¬ą┬Ą─▓▀┬į└┤─▓╚Īš■ų╬└¹ęµŻ¼Į½Ž╩╗ŅĄ─╬▐╣╝╔·├³Ą▒│╔Ęų┴č╗ŅČ»Ą─╣żŠ▀║═╗±Ą├╬„ĘĮį«ų·Ą─│’┬ļĪŻĪČ╗ĘŪ“╩▒▒©ĪĘ╝Ūš▀2012─Ļ10į┬╔Ņ╚ļ┤’└╝╚°└Ł╠ĮĘ├Ż¼ū▀Į³┤’└╝╚°└ŁĄ─╦┬├ĒŻ¼ūŅŽ╚┐┤ĄĮĄ─╩Ūą³╣ęį┌═ŌĄ─ūįĘ┘▓ž╚╦Ą─Š▐Ę∙║Ż▒©ĪŻ2012─Ļ11į┬ŪÓ║ŻŠ»ĘĮėļ╦─┤©Š»ĘĮŽÓ╝╠šņŲŲ┴╦ūįĘ┘░Ė╝■Ż¼ėļ┤╦═¼╩▒Ż¼│¶├¹ščų°Ą─ĪČūįĘ┘ųĖĄ╝╩ķĪĘę▓▒╗╣·─┌═Ō├Į╠ÕĮę┬ČŻ¼ŲõųąūŅ╬³ę²šŌą®╬▐╣╝╔·├³Ė╩įĖ╬■╔³Ą─ę╗╠§▒Ń╩Ū╦└║¾┐╔ęįĄ├ĄĮ┤’└Ą└«┬’▒Š╚╦Ą─Ą╗Ėµėļ╝ė│ųĪŻšŌę╗╣½╚╗└¹ė├┤’└Ą└«┬’Čį¾Ųą┼ū┌Į╠Ą─▓žūÕ╚╦Ą─ė░Žņ┴”╗±╚Īš■ų╬└¹ęµĪóĮ½╬▐╣╝╔·├³Ą▒│╔▓┘┐ž╣żŠ▀Ą─ąąŠČŻ¼┴Ņ╩└╚╦╗®╚╗ĪŻę╗╬╗ėó╣·═°ėčĖ°ųą╣·╬„▓ž═°┴¶čįŻ¼│Ų╩«╦─╩└┤’└Ą└«┬’Ī░ū┌Į╠ąķ╬▒Īó╠¶▓”└ļ╝õĪóųŲįņ▓╗║═ĪóČį╩└Įń║═ŲĮ╬▐╦┐║┴╣▒ŽūĪ▒ĪŻ
ĪĪĪĪę╗ĘĮ├µ╩Ū╚ĪĄ├├└╣·┬╠┐©Ą─╦∙╬ĮĪ░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╣┘į▒į┌╣─└°▒Ż│ų─č├±╔ĒĘ▌Īóą¹Į▓Į╠╦¶Ęų┴č╗ŅČ»Ż¼Č°ūį╝║╣²ū┼ū╠╚¾Ą─╔·╗ŅŻ╗┴Ēę╗ĘĮ├µ╩Ū╩▄╣Ų╗¾Č°Įß╩°Ą─╬▐╣╝╔·├³║═▒╗▒▀įĄ╗»╣²ū┼Ų»▓┤▓╗Č©╔·╗ŅĄ─Ųš═©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ĪŻŽ╩├„Ą─Čį▒╚Ż¼┴Ņ╚╦═┤ą─ĪŻ
ĪĪĪĪ▓žūÕĪ░╣┬Č∙Ī▒╩┬╝■ 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▒»▓ę├³į╦Ą─╦§ė░
ĪĪĪĪ╚ź─Ļ│§Ż¼╚╩┐Ą╝č▌╬┌└’Īż├ĘČ¹┼─╔ŃĄ─ĪČ╠ß▒╚║═╦¹Ą──ĖŪū├ŪĪĘ╝═┬╝Ų¼╔Žė│Ż¼Į▓╩÷┴╦ę╗Ė÷▓žūÕ┴„═÷Č∙═»╠ß▒╚Ą─├³į╦Ż║1961─Ļ╔·╗Ņį┌┤’└╝╚°└ŁĄ──č├±ė¬ųąĄ─7╦Ļ╠ß▒╚į┌▓╗ų¬ŪķĄ─Ūķ┐÷Ž┬ū„╬¬╣┬Č∙▒╗╦═ĄĮ╚╩┐╩šč°Ż¼Ą▒╦¹╚╦ĄĮųą─Ļį┘╝¹ĄĮ─ĖŪū╩▒Ż¼ę芣▓╗╗ß╦Ą▓ž╬─Ż¼─ĖūėŽÓ╝¹╚┤▓╗ŽÓ╩ČĪŻ╚├╩└╚╦ŪÕ│■Ąž┐┤ĄĮ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▒»▓ę├³į╦Ą─╦§ė░ĪŻ
ĪĪĪĪ║¾└┤├ĘČ¹į┌Įė╩▄╚╩┐ĪČą┬╦š└Ķ╩└▒©ĪĘ▓╔Ę├ųąĮ°ę╗▓ĮĮę╩Š┴╦Ą▒─Ļ▓žūÕĪ░╣┬Č∙Ī▒Ą─įŁ╬»Ż║Ī░ūį1960─ĻŲŻ¼╚╩┐Ų─ėąė░Žņ┴”Ą─╩ĄęĄ╝ę░¼ŽŻ┬³ėļ┤’└Ą└«┬’┤’│╔ąŁęķŻ¼Į½200├¹▓žūÕĪ«╣┬Č∙Ī»Į╗Ė°┼Ęų▐╩šč°╝ę═źĖ¦č°Ż¼╗“╩Ū╦═ĄĮĄ▒ĄžĄ─Č∙═»┤ÕĪŻĄ½╩ŪšŌ200├¹Č∙═»ųąų╗ėą19Ė÷╩ŪĖĖ─Ė╦½═÷Ż¼Š°┤¾ČÓ╩²║óūėų┴╔┘ėąĖĖŪū╗“─ĖŪūŻ¼ėąę╗ą®╔§ų┴╦½ŪūČ╝ĮĪį┌ĪŻ┤’└Ą└«┬’ų«╦∙ęįę¬╦═│÷šŌą®║óūėŻ¼įŁę“į┌ė┌╦¹Žļ╚├šŌą®║óūėĮė╩▄╬„ĘĮ▒Ļū╝Į╠ė²ų«║¾│╔╬¬╔ń╗ߊ½ėó╚├╬„▓ž═č└ļųą╩└╝═Į°╚ļŽų┤·ĪŻČ°Š▌═│╝ŲŻ¼Į÷į┌Ąų┤’╚╩┐║¾╝Ė─ĻŠ═ėą┤¾į╝90ŻźĄ─Ī«░¼ŽŻ┬³Č∙═»Ī»Ę┼Ų·┴╦▓žė’Ż¼╦¹├Ūį┌╚╩┐│Ż│Ż▒╗ŽĘ┼¬Ż¼╔§ų┴ėąūį╔▒ąą╬¬ĪŻĪ«░¼ŽŻ┬³║óūėĪ»ėļ┤’└Ą└«┬’Ą─│§ųį▒│Ą└Č°│█ĪŻĪ▒
ĪĪĪĪĪČą┬╦š└Ķ╩└▒©ĪĘį┌┐»ĘóšŌŲ¬ū©Ę├╩▒Ż¼Į½▒Ļ╠Ōą┤╬¬Ż║┤’└Ą└«┬’Ą─Ą└ŪĖ╩«Ęųųžę¬ĪŻ╚╗Č°Ą└ŪĖėļʱėų─▄Čį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Ą─╔·┤µĪó╔·╗Ņū┤┐÷Ą─Ė─╔ŲŲĄĮ╩▓├┤č∙Ą─ū„ė├─žŻ┐Ų»▓┤▓╗Č©Ą─╔·╗ŅĪó╩▄ĄĮŲń╩ėėļ─«╩ėĄ─Š½╔±╩¦┬õ╝Ė║§│¼╣²┴╦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ū„╬¬ĘĮ╠═Į─▄╣╗╚╠╩▄Ą─Ž▐Č╚Ż¼║▄ČÓ╚╦▒Ē╩ŠŽŻ═¹─▄ėą│»ę╗╚šĘĄ╗ž╣╩ŽńŻ¼Įß╩°┐═ŠėęņŽńĄ─╔·╗ŅĪŻ
ĪĪĪĪ╗žĄĮūµ╣· ╗žĄĮ╣╩Žń
ĪĪĪĪĪ░80║¾Ī▒═·─Ę╩ŪĖ╩╦ÓĖ╩─Ž┬ĄŪ·▓žūÕųąč¦Ą─ę╗╬╗ą┼Žó╝╝╩§Į╠╩”Ż¼╦²ėąę╗Ė÷╝┤Į½╚²╦ĻĄ─Č∙ūėŻ¼Ė·ļŻ±¾ų«─ĻĄ─═Ō╣½═ŌŲ┼╔·╗Ņį┌ę╗ŲŻ¼╦─╩└═¼╠├Ż¼Ųõ└ų╚┌╚┌ĪŻĄ½║▄ČÓ╚╦ę▓ąĒ▓ó▓╗ų¬Ą└Ż¼╦²Ą─═Ō╣½═ŌŲ┼╩Ū1986─Ļ┤ėėĪČ╚╣ķ╣·Ą─▓ž░¹ĪŻ
ĪĪĪĪ═·─ĘĄ─═Ō╣½╔·ė┌1929─ĻŻ¼╩ŪĖ╩─Ž┬ĄŪ·╚╦ĪŻ1958─ĻŪ░═∙└Ł╚°─▒╔·║¾▒╗╣³ą«│÷ū▀ėĪČ╚ĪŻ1986─ĻŻ¼═·─ĘĄ─═Ō╣½╩šĄĮųČČ∙Ą─└┤ą┼Ż¼╦Ą╦¹Ą─Ą▄Ą▄╚ź╩└┴╦Ż¼╦¹Ą──ĖŪū─Ļ╩┬ęčĖ▀╔Ē╠Õ├┐┐÷ė·Ž┬Ż¼Č°╝ęŽńĄ─╔·╗Ņ╠§╝■ę芣▒õĄ├║▄║├Ż¼ŽŻ═¹╦¹─▄╗ž└┤ĪŻ├µČįŪūŪķĄ─š┘╗ĮŻ¼═·─ĘĄ─═Ō╣½į┘ę▓Ąų▓╗ūĪČį╝ęŽńĄ─╦╝─ŅŻ¼Ū░═∙ųą╣·ūżėĪ┤¾╩╣╣▌╔ĻŪļ╗ž╣·ĪŻ
ĪĪĪĪ│÷║§╦¹ęŌ┴ŽĄ─╩ŪŻ¼╔ĻŪļ╗ž╣·▓ó├╗ėąŽ±╦¹ų«Ū░ĄŻą─Ą──Ūč∙╩▄ĄĮ┤¾╩╣╣▌Ą─Ą¾─č╗“Š▄Š°Ż¼╝Ė╠ņŠ═╔¾┼·Ž┬└┤┴╦ĪŻĖ³╚├╦¹├╗ėąŽļĄĮĄ─╩ŪŻ¼╗žĄĮ╝ęŽń║¾Ż¼Žžš■Ė«Ė°▒©Ž·┴╦╗ž╣·Ą─┬ĘĘčŻ¼╗╣░’╦¹├Ūį┌Žž│Ūą▐Į©┴╦╦─Šė╩ęĄ─ą┬▓žĘ┐ĪŻ═¼╩▒Ż¼╦¹ū„╬¬╣ķ╣·▓ž░¹Ą─┤·▒ĒĄ▒čĪŽžš■ąŁ╬»į▒▓╬š■ęķš■ĪŻ
ĪĪĪĪĪ░╝ęŽńĘó╔·┴╦ĘŁ╠ņĖ▓ĄžĄ─▒õ╗»Ż¼╔·╗Ņ╠§╝■▒╚ęįŪ░║├┴╦║▄ČÓŻ¼ū┌Į╠ą┼č÷ę▓╩Ūūįė╔Ą─Ż¼╗žĄĮ╝ęŽń╩Ūę╗Ė÷š²╚ĘĄ─čĪį±ŻĪĪ▒└Ž╚╦╦ĄĪŻ
ĪĪĪĪ2003─ĻŻ¼ĄžĘĮš■Ė«╬¬─Ļ┬§Ą─└Ž╚╦╦½╦½╔Ž┴╦Ą═▒ŻŻ¼├┐į┬│²┴╦š■ąŁ╬»į▒Ą─▓╣╠∙╗╣ėąūŅĄ═╔·╗Ņ▒ŻšŽĮĪŻĄžĘĮ═│šĮ▓┐▓ž░¹░ņĄ─╣żū„╚╦į▒├┐ĘĻ─ĻĮ┌Č╝╗ß┤°ū┼╬┐╬╩ĮĪó├ūĪó├µĪóė═Ū░└┤╠Į═¹┴Į╬╗└Ž╚╦ĪŻ
ĪĪĪĪ═·─Ę╦ĄŻ¼╦¹Ą─═Ō╣½═ŌŲ┼╚ńĮ±ę└Š╔▒Ż│ųū┼ĘĮ╠═ĮĄ─╔·╗ŅŽ░╣▀Ż¼ū¬ŠŁĪó│»ĘŻ¼Ė·Ą▒ĄžŲõ╦¹Ą─▓žūÕ└Ž╚╦ę╗č∙Ż¼▓ó├╗ėą╩▄ĄĮŲń╩ė╗“Ū°▒Čį┤²ĪŻ┴Į╬╗└Ž╚╦─Ņ─Ņ▓╗═³Ą│║═š■Ė«Čį╦¹├ŪĄ─╣ž╗│šš╣╦ĪŻ
ĪĪĪĪ1978─Ļ╩«ę╗Įņ╚²ųą╚½╗ßų«║¾Ż¼ųą╣·š■Ė«ųŲČ©┴╦Ī░░«╣·ę╗╝ęŻ¼░«╣·▓╗ĘųŽ╚║¾Ī▒ĪóĪ░└┤╚źūįė╔Ż¼╝╚═∙▓╗Š╠Ī▒Ą╚╗ČėŁŠ│═Ō▓ž░¹╣ķ╣·Ą─ĘĮšļĪŻ1979─Ļį┌ųąčļš■Ė«š■▓▀Ėąš┘Ž┬Ż¼ęį╝░į┌╬„▓ž╔ń╗ßĮ°▓ĮĪóŠŁ╝├Ęóš╣Īó╚╦├±╔·╗Ņ╦«ŲĮ▓╗ČŽ╠ßĖ▀Ą─╬³ę²Ž┬Ż¼ąĒČÓ╣·═Ō▓ž░¹┐¬╩╝ĘūĘūĘĄ╗ž╬„▓žĪó║═╦─╩Ī▓žŪ°Ż¼╗ž╝ęŽń╠ĮŪūĘ├ėčĪó│»ĘĪó▓╬╣█Īó░ņ╩┬ĪŻ╬„▓žūįų╬Ū°║═└Ł╚°╩ą╚╦├±š■Ė«╗╣┴¬║ŽŽ┬Ęó┴╦ĪČ╣žė┌╗ž╣·Č©Šė▓ž░¹░▓ų├╣żū„ųą│÷ŽųĄ─╬╩╠Ō║═ĮŌŠ÷ęŌ╝¹ĪĘŻ¼Čį╗ž╣·Č©Šė▓ž░¹Ą─╔¾┼·╩ųą°╝░Š▀╠Õ╬╩╠ŌĄ─ĮŌŠ÷░ņĘ©ū÷┴╦├„╚Ę╣µČ©Ż¼░³└©ĮŌŠ÷ūĪĘ┐ĪóŠŁ╝├▓╣ų·Īó░▓┼┼Š═ęĄĪóĘó╗ėĖ÷╚╦╠ž│żĪó╣žą─╔·╗ŅĪó╚©└¹Ą╚ĘĮ├µĪŻ
ĪĪĪĪĮ³Ų┌╗ž└┤╠ĮŪūĄ─Ī░80║¾Ī▒├└╝«▓ž░¹į·╬„Ż©╗»├¹Ż®į┌Ė·╝Ūš▀ė├ėóė’Į╗╠Ė╩▒Š═▒Ē┤’┴╦ŽŻ═¹╗žĄĮ╣╩ŽńĖ╩─ŽĄ─įĖ═¹Ż¼ę“╬¬į┌╦¹Ą─č█└’Ż¼╣╩ŽńĄ─╚╦├Ū╔·╗Ņ╩ŪąęĖŻĄ─Ż¼╦¹├Ū╝╚▒Ż│ųū┼┤½═│Ą─ė╬─┴╔·╗ŅŽ░╣▀║═│»Ę└±ĘĄ─Ž░╦ūŻ¼ę▓ŽĒ╩▄ĄĮ┴╦Žų┤·╗»Ęóš╣Ą─▒Ń└¹Ż¼Ęó┤’Ą─╣½┬ĘĪóĄń╩ėĄń╗░Īó═°┬ńĄ╚Ą╚ĪŻ ╦¹╦ĄŻ¼Ī░š■Ė«─▄╣╗╚├╬ę╗žĄĮ╝ęŽńŻ¼Čį╬ę║═╬ęĄ─╝ę╚╦└┤╦ĄęŌęÕųž┤¾Ż¼╚├╬ę├ŪĮß╩°┴╦ŪūŪķŽÓ╦╝Ą─╝Õ░ŠĪŻ╬ę╗ž└┤╠ĮŪū╩▒Ż¼ĄžĘĮš■Ė«Ą─╣żū„╚╦į▒ę▓ū▄╗ߊŁ│Ż╬╩╬ęėą├╗ėą└¦─čĪóąĶ▓╗ąĶę¬░’ų·Ż¼╦¹├ŪšµĄ─║▄║├ŻĪĪ▒
ĪĪĪĪėļšŌą®╣ķ╣·Č©Šė║═╠ĮŪūĄ─▓ž░¹ŽÓ▒╚Ż¼ų═┴¶į┌Ī░┴„═÷š■Ė«Ī▒╣▄ŽĮų«Ž┬Ż¼ęįŠ█Šėį┌┤’└╝╚°└Ł╬¬ų„Ą─Ī░┴„═÷▓ž╚╦Ī▒├ŪŻ¼Čįė┌Žń│ŅĄ─╚╠─═ėų─▄╚ń║╬┼┼ĮŌŻ┐Čįė┌╬┤└┤╝╠ą°Ų»▓┤Ą─╔·╗ŅėųĮ½╚ń║╬ė”ČįŻ┐Čįė┌▒╗Ęų┴č╩Ų┴”║═▒ėąė├ą─ų«═ĮĄ─Ī░Ž┤─įĪ▒║═└¹ė├ėųĮ½╚ń║╬Ąųė∙Ż┐Ė÷ųąū╠╬Čų╗ėąĄ▒╩┬╚╦▓┼─▄╠Õ╬ČŻ¼┴Ņ╚╦▀±ąĻĪŻ
>╣·─┌ą┬╬┼Š½čĪŻ║
- Īż╔┬╬„Ż║╩Ī─┌╗ßęķ╗ŅČ»Čį┴ņĄ╝│Ų║¶▓╗╝ėĪ░ūŠ┤Ą─Ī▒
- ĪżŪÓ║ŻŻ║┼«ų░╣żŠŁŲ┌▓╗─▄╝ß│ų└═Č»┐╔Ė°ėĶ╣½╝┘ę╗ų┴Č■╠ņ
- Īż╣ŃČ½╚ĪŽ¹į▌╗║Š═꥚■▓▀ Ė▀ąŻ▒ŽęĄ╔·į±ęĄš■▓▀8╚š╩Ą╩®
- Īżųą╣·║ŻŠ»2305Įó═¦▒ÓČė8╚šį┌ųą╣·Ą÷ėŃĄ║┴ņ║Ż─┌č▓║Į
- ĪżųąĘĮ▓Ą│Ō─©║┌ųą░═ŠŁ╝├ū▀└╚Į©╔Ķ▒©Ą└Ż║▓╗Ę┴╩ĄĄž╚ź┴╦ĮŌ
- Īżą▄šū╚╩╩┼╩└╩┬╝Żį°▒╗┼─Č╔ĮŁšņ▓ņ╝Ū ┐¬╣·Į½ąŪĮ÷┤µ12┐┼
- ĪżĮŌ┬ļą█░▓Ų¶Č»Ū°Ż║╬┤└┤20ĘųųėĄĮ▒▒Š®┤¾ą╦ 30ĘųųėĄĮ╠ņĮ“
- ĪżĮ³╩ėĮ├š²┴ņė“┬ęŽ¾ŲĄĘó 6▓┐├┼┴¬║ŽĘó╬─╝ėŪ┐╝Ó╣▄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