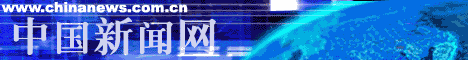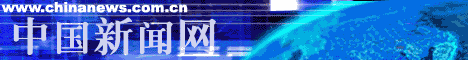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: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Ȩ��ע��ժ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绰:68994602)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ڳ�Ϊ�ִ�����֢��Ⱥ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ߵ���ع���ҲҪ�ﵽ180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硪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֪���ⲡ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/���
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7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Dz�һ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1���ʱ��С���Ѿ���ʶ200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˵Ĵ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һ�ж�����2��ʱ��ֹ�ˡ�2��ʱ��С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仯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κ�Σ�գ��Ա��˵�ϲŭ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⸸ĸ�Ĵ��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Ϊʲô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,��ͻȻ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ռ䡣
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ʶ�ְ����衣
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С��һ���ĺ��ӣ����й���صĹ�����180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䶥���Ĺֲ�
����С���İְ���־�٣�����1998���֪С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־�پ�ְ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Ӹշ����仯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ݶ�һ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ǹ����æ��ʱ���ڵ绰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־�ٺ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ܡ���ʺ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绰Խ��ԽƵ�������ҲԽ˵Խ���أ����ɴ�ÿ������绰�Ϳޡ�����־�ٻ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ҵ�ʱ��Ϊ�Ұ��˷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ʱ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��¶�֢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ٲ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ֲֹ���С����ô���ܣ���
����1998��8�£���־�ٴӹ��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ú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һ�ؼ��Ҿ�ɵ�ˣ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κγ���С��ֻ֪������Ŀ�ĵ��ܣ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ֶθ���û�а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ʱ��ȫ��ᵽ�˰����ڵ绰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ֿ��µ����Ρ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־���ҵ���ʱ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¶�֢��ҽԺ֮һ��ҽ��Ժ��ҽ���۲��˺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ӻ��ж�ͯ�¶�֢��Ҳ���Ա�֢����һ��ȫ�淢���ϰ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䶥������־�ٻ��䵱ʱ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ͺ�ĸо�˵���ܶ�¶�֢���ӵļ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
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ޱ���ȫ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硣�����180���ƣ�һ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6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¶�֢�漰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1080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ݣ�ŷ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ʵı���Ϊǧ��֮����ǧ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ô�й��Ŷ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30����780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ǣ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0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֢�ķ����ʺ����塢������ỷ����û���κι�ϵ��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¶�֢�ķ�����Ҳ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־�ٳ���ؿ����Լ��ĺ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ĸ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ƾ������ٰ�ǻ�����ƾ���뾡�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˻���Ц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
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ദ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ʹ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û�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־�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ⲻ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ؽ��Ӵ˸ı䡣
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ֲ��ĺ�����Ҫ�ҳ���ȫ����غ���־��˵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籣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ȶ��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չ˺��ӺͲ��ܼ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Ҫ�ܶ�Ǯ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ܴ�Ҳ����óȻ��ְ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Ҳ���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ǿ����Ϊѵ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Լ���յ����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˹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Ǹ���ɫ����λ�¶�֢���ߣ��ⲿӰ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븶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չ˺��Ӱɣ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ܿ��ź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ȥ�����˵��С��һ�ҵı��磬�ڼ���ÿһ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ļ�ͥ�ж����ݹ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λ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չ˺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ƽ˵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Ϊ�¶�֢��ͥ�ṩ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й��¶�֢Ⱥ���е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߲ɷ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й¶�֢�ĺ��ӣ����ĸ�ĸһ�㶼�����ʱȽϸߵġ��Բ���ǰ�ڱ�����һ�ι¶�֢�����ҳ��ۻ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ר�ҡ�����ר�һ��ǵ¹�ר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ҳ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Ӵ�����30��λ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õ�˶ʿ����ʿѧλ�ľ���6λ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֮�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ҳ���ʱ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ɱ�̫���ˡ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켯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ߵļҳ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Թ¶�֢��Ⱥ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ӵļҳ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ļз��С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1989�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μ�ֵ
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ֹ۵�Ů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ĺ�����й¶�֢ʱ��ͬ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Ǻ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ڴ���ϣ�ֻ���롪��˭�ܰ��ң�˭�ܸ����Ҹ���ô�죿�����ƽ��14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ֹס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е�ȥ����ȥ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й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˭���չ����ĺ��ӣ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硣
����1993�꣬���ƽͨ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ѯ���ϣ��Թ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⡣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ר�Ÿ��¶�֢��ͥ�ṩ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3��15�գ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ꡱ10������ա�10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ꡱ�ı��˺ܶ��ͥ��֪����ľ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ϸı���һЩ��ͥ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֢��һ�־��μ�ֵ���ķ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ίԱ�ḱί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˵����ֻҪ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ȷ�ķ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ξ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3��6�ꡣ��
����ֵ��һ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ֹ¶�֢�����߱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챦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һλ�¶�֢���ߣ���ͬʱ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���ʦ����Ҳ�ǰ�����˾˵���Ⱥ��֮���Ծ��μ�ֵ����ԭ��֮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¶�֢���߿��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ף�Ʃ�续����ߣ�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λ58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ˣ���1995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й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Ѿ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ˡ����й��Ŷ�֢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ʵ��ϣ����Ҳ�ǡ������ꡱ10�����й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˵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Ϊ2060λ�¶�֢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ͥ�ṩ����ѯ������Ϊѵ������ͥѵ��ָ�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ӡ�ʯͷ���ָ��þͺܺá�
����ʯͷ����12�꣬��2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˲�֢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룬Ȼ��Խ��Խ��Ƨ���ܾ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4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ͷ����ʼϵͳ�����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磬�����ֶε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�˵���ӷ����ˡ�ʯͷ���й¶�֢�����㲻��ѧϰ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3��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ѧ�ļ��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ɷ�ʱ����ʯͷ��Ҳ�ڼҡ������á�ʯͷ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ʯͷ���ͺܸ��˵ش��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Ͱְ����졣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۶���ʿ�İְ֣��ǡ�ʯͷ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Dz�ʿ���Ұְ��ǡ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ʯͷ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ڡ�ʯͷ���ڵ���ijһ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꼶���ɼ�����ǰé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ѧ��óϵ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ൺ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Ան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3��15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¶�֢�ġ��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ϯ�����˱�ʾ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ꡱ�����й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ʶ�����ƹ¶�֢�Ŀ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ӡ�ʯͷ���Ļָ������˹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ָͥ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ֻ֢Ҫ�ֶεõ������Իָ�������״̬��
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ƹ¶�֢����ȡ�õijɼ�֮һ���ǣ��ںܶ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ꡱ�͡����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ˣ�ȴû��ѧУ���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ij�ַ�ʽ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¶�֢���ӵļҳ�֣��(����)�����κε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й¶�֢��֣�õĺ�����ѧУһֱ�ܵ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ת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Ӵ�Сѧ����ѧ��һֱ�ǡ����λ�ʽ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�ģ�շת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
����û��ѧ�ϵ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ѧУ�ﱻ�����ҳ�Χ��3��Сʱ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ҳ��Թ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ϰ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ѹ���ĸ��ܣ����ǹ¶�֢�ĺ��Ӿ�û��ѧϰ��Ȩ�����𣿡�֣��˵��һЩѧУ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ȷ�ܾ����Ӿ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й¶�֢�ĺ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䶼������ѧ�ˣ�����ȴһֱû��ѧУ�Ͻ��գ��ҳ�ֻ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ѵ�౨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ѧʲô������Ϊ�˸������ṩһ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Ļ��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ӱ�һ��ѧϰ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ȥ��һ���µ�ѧϰ�ࡣ���ļҳ���Ϊ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շת����ѧҲ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Ҫ�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ڶԹ¶�֢�IJ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ڵŶ�֢�����ձ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㷺���ܵ�;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һ��̸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պ����ѧ��ҵ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ίԱ�ḱί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й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ѧȨ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ѧУ�DZ�����ܹ¶�֢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���һ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¶�֢��ɥʧ�����Ҵֹ¶�֢�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ϣ�ֻ����Ϊ��Щ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Ƚϵͣ�Ϊʲô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ѧУȥѧϰ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ǵģ��ǹ¶�֢���ӳ����ľ�ҵ���⡣�ܶ�ҳ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ʣ�º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мҳ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һ�ٱ�ʾϣ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֢�Ļ���ʵ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Ƿdz��º͵ģ��¶�֢�ĺ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ǣ���Ӧ�ûؾ����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ҵķ�չˮ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ҲҪ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̬�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ָ�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ѧ���õĴ�̨���ϿΣ���ͬѧ�Ǻ���ʦ�Dz�δ�Դ��кβ�Ѱ���ķ�Ӧ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⺢�ӡ��ļҳ��Ƕ����룬�Լ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һ�졣
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ൺ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Ան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�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滹��200�����Ŷӵ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ꡱ�Ľ�ʦ������30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10���нӴ��Ŷ�֢�����ﵽ10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Ϲ¶�֢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Ȩ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й�Ŀǰ�¶�֢ʦ�ʵ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ļ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䷢�𣬸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һ���ָ��Ļ��ᣬһ���ָ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Ҷ����ף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ίԱ�ḱί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3��1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صļ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û�м�λ�ٷ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Ҳμӣ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ź�����Ϊ��Щѧϰ��Ӧ����ר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ھ�Ȼ�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��20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ٿ���һ�ι��ڹ¶�֢�����ľ��齻���ᣬ����ר�ҵ��ᡣ�ⱻ��Ϊ��ζ���й��Ŷ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µIJ��档
�����˼䣬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ؽ̴������ܵ�ï��ʾ: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ܶ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ѧϰ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ͨѧУ���е����ؽ�ѧУ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ֻҪ��Ӱ���ճ�ѧϰ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ͯ��ѧ�Ѿ�����ܾ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ï�Ľ��ܣ����й��ܶ���к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㽭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㶫�ȣ����й¶�֢�����Ĺٷ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롣����Ҳ���ϣ�Ŀǰ���¹¶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û�о�����ѵ��ȫ�Ƿ�רҵ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Ĺ����йأ����ܼغͷ�����ҽ��бȽϡ����ܵ�ï˵�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˸е���ֵ��ǣ��й��¶�֢�Ĺٷ��ٴ룬�����ٷ��о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ĩ�Ϳ�չ�ˣ�ȴ���мҳ�֪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94�ꡫ1996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飬��6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8���¶�֢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κ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һ���̶ȵĽ�����1999���ֿ�ʼ��һ�ε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ʼ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ƹ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˹¶�֢�о���ѧ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ܶ���ļҳ�����ʾĿǰ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ѧ�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顣
�������ֹٷ��о���Ͷ��ͼҳ��õ���Ϣ֮�䲻�ԳƵ���״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Գ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ڽ����еŶ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ļҳ��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2003���16�ڣ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