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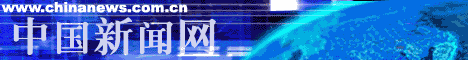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dz���Ҫ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̶ȡ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硸�Һܹ��㡹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Ҫ�õ��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���ָһȺ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硢˼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Ч�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ں�֮�ޣ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С����Դ��Ȼ�ѷ������Թ�ʢ��˧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ڣ�ľ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¡ʷ����ԭ�硢���̹��ӡ��ɵ��˲��ӡ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г���ƾ�贿�顢��ʳ�˼��̻����ôһȺż��ȡ���й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ֳ��˼���ij�ݺͰ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ձ�ż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Ǯ��Ϊ�ľ��Ǵ��㡸�վ�ȫ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ӡ�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Ȼ�Dz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˵���վ簮��Ƭ֮���䣬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һ�Ƕ��顷�����վ��һ����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Ƶĺ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㣬���Ƿ��¡ʷ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˾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գ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ֹ��еĿ����ˡ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˹�ڼ�ʮ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յ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ǵ�ϣ�����й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��ǿ���֮�ԣ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գ�ȴҲ���ò���һЩ��ʶ֮ʿ���ǡ����ǵĺ��ӣ�Сʱ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��˵ġ�С�ʵ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ҡ��һ���Ϊ���ձ��Ļ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˲�֪���θ��롣 �����й�Ҳ��ʼ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Լ���ż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½�㡢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쾲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˧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Ƥ�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档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Ų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ƹ���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й�Ӱ�ӣ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ձ��˵��й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ij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ٸ�ߣ���ѧѧ���Ƿ����ˡ��պ��¼��ನδϢ���̿���粨��ƽ��С�ձ���Щ����̫���ˡ���Ȼ�Ļ�Ȧ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Σ����ձ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Ӫ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ʵ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Ƥ�ܵ�˵���й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塹��ȴ���IJ��ĵظ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ⲻ���й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Ϳ־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Ļ�DZ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еĺ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ӡ�ڮ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ձ�ʱ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Ĥ�ݣ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η 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ܻ�������ô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ӣ���Ƶ�ͷ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˳�ڷ���Ʈ�衢�ͷ�ѣĿ���ɸ�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A�ο㡭����Щ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㣬���Ǿ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塣
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ģ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˵ģ�ǡǡ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ǶԼ�Ҳ�����ж��ӡ���ϲ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ܰ������Ե�ͷ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Լ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裬����һ��ʼ��֪����ֵĺ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塹�Ժ�����ע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ƣ�Ѱ���Ÿ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ͬ�����ԡ��ĺ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Ǵ��ִ�ŵ����Ÿ�ĸ��Ǯ���Ѹ�ѧ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֮�⣻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ܰѸ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ͺš��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ĵ�·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ݾ���һ���죬��Ļ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Զֻ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Ⱥ�Ҵ�ææ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õ�Ů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Ҫ��ȥ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ࡣ�ܹ�ѧϰ���˵ij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ã���Ȼ�Ǻ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Ҫѧ�ա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ѧ���ǵĻش����ҳԾ��ˣ���Ȼ��Ϊ�˿����ձ�ż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ԡ�ԭ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С������˹�Ļ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һζ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أ�ժ�ԡ��Ļ��¿���2001.6. 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