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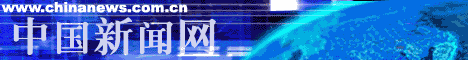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ͱ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ʫ�ˡ��Ĵ����棬�Զ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ʫ�˵�����Ʒ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ʫ̳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ָ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ʫ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롣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ʱ��ÿ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ˮ���ڳ��ŵ�ɡ�ϣ��δ�δ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ڡ��� 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Ǵ�С�ܵ������ر�谮��Ե�ʣ���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ټ̳���ʫ�˵�ij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ѧר�ű��˱��⡣�ɷ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ܰ�Ļ��ݺ���Ʒ��ů�ţ�����٩٩��̸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ңԶ��ʫ�⡣ ���ۡ�֮־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״�����ԭ�DZ����ӻ�վ����ְͨԱ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7��ʱ�ټ�Ǩ�غ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ְԱ��ĸ�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ڣ���δ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ƹʣ����ܳɱ��ؽ�����ˮ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ǡ��ȹ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Ȥ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컨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ÿɰ������ݡ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ȱ�ݣ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İѱ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ȡ��һЩ�ɾ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ͬ�еij�Ц��1931��12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ͬѧ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Ϸ���һƪ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ӵı�������С˵��С˵�ز�֮һ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ݡ������DZȴ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ʫ�ˣ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ݣ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Ǯ��˭�������˭���ˣ��ò��ã����Ȼ��ָ�ҡ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ұ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˭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Ȥζ��˭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û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Ȥζ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IJ��Ҳ�̲�ס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볰Ц�еĴ����棬ֻ�а�Ωһ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ھ����µ�־Ը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ŵ��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ijһ�����ǿ�֡� 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28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ذ�����ʩ�ݴ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ʱ��18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ÿ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γ�ǿ�ҵĶԱ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ı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д�����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˵�ҵ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ɬ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ɬ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浱ʱ�ľ����Ϻ�ʩ�ݴ洦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ʫ���ף���ʩ�ƽƫƫЦ�����𡣶�ʩ�ƽһ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ӻ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¥��Ю��Ҫ��ʩ�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䣬��ǿ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֮�ʣ��Ͻ�Ҫ��ĸ�Ӻ��ݸϵ��Ϻ�����ʩ�ĸ�ĸ���ס�ʩ�ƽ��ĸ����Dz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ʩ�ݴ��Ŭ���£�Ҳ��ǿͬ�⡣
����1931�괺��֮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ƺ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ӡ��Ϊ�˶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еĴ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ظе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ҿ�ʹ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ʹ�ĵ��ǻ��ֵ��ģ�����СС�ĺ����۷䡣���ҵ����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Ԥ�й���õ���֤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ȡ��ѧҵ�����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ȡ���Ϊ��̫��ʩ�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1932��10��8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÷dz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£�Ϊ�˶��ְ����Ԥ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ذ����ʴ��뻦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 ����8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��3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ѧ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ֻ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1933��3��5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Ҳû�У�Ҫ���飬ͬʱΪ������Ĺ�ϵ���ֲ��ò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С���鰸�ϣ��ڿ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ӱߵ�ÿ��ɢ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1933��8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סƶ������д�Ÿ��߸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æд�Ÿ�֪ʩ�ݴ棬ʩ�ݴ�Ѹ�ٵ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ؿ��ǻع�һ�¡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Ҫ�ع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Ǯ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ﰺ�з���ѧ����Ӽ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ʫ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ѡϰһ����ƾ��ѧ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һ�꣬�ڶ��꿼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Dz��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ݴ��ص�ȥ��ף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ﲢû�кú�ѧϰ��ֻ�����Ѵ˵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϶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1934��8�£���ʵ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Ĺʾ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ʫ�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빤���ṩ��ֱ�ӵ��زġ� ����1935��4�£������汻�з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Ϊ���з���ѧס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ɼ��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ڷ�����˹ʾ�����С�ֱ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ϳ�ʱ��ֻ�����һ��Ϊ�����У�ѧУû�и���;�е�����Ǯ��ֻ��һ�Ż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ĵȲյĴ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Ȳգ��ĵȲ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û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1935��5�´�����ص��Ϻ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ŵĴ������ڵõ�֤ʵ��ʩ�ƽ��ȷʵ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Ǹ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֮�µ��ڴ���ʩ�ƽһ�Ƕ��⣬����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ζ��ݵ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ʹ�еĴ����棬��ʱס������Ÿ�Ľ��幫�Ĺ�Ԣ������ʱӢһ�Ұ��úܽ���Ϊ�˸�ο�����氮����˿ڣ���ʱӢ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档С��1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崿������һ�¾���ס�˴����棬ʹ���ܿ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ڶ����顣��1938��5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Ϻ��˴�����ۺ�����֮��ĸ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˷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¶��ɸ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˭Ҳ����˭��ʲô����ʲôʱ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ܣ��ҳ�ȥ����Ҳ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ʲô���飬���ĸ����ʩ�ƽ�ˡ��� ����1940�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Ҿ�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û��ķ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㽫���ᰮ�ҵġ�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Ҿܾ�����Ϊ��䣨��Ů����ӽ�أ��Ѿ�5���ˣ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ú��ӿ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ʹ��õ���š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⡸�����项д������˸У�����δ�ܶ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Э����ǩ�֣�����Э�飬��ӽ�ع�����渧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42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ڴ�ͬͼ��ӡ��ֵij�дԱ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21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˻顣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ö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16�꣬���ڱ˴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죬��֮��ǰȱ�������˽⣬��ñ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ϵ��Ѻ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³��ܡ�1948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ղ̵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 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194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ʤ������Ϣ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ա�ԩ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֮�մ�Ӣ���ع���·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۴���ȥ�ˣ�һ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Ҫ���ù���һ�㡣���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Ե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ͽ��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汻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ָ����Ŀ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˺���ľ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ĸı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¥��Ҫͣ������Ϣһ�����Ϊ�˸��õ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鲢δ��ת�����ڵ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��ķ��ķ��룬����ǰ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ڼ����ơ�1950��2��28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ã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ڴ��Ͼͻ��Թ�ȥ�����͵�ҽԺ���Ѿ�ֹͣ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Ҳ�6�ꡣ�ҵ�ʱ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ȥ�����Ҹе��ܺ��£�ֻ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ܵ���Һ�Զ��Ƨ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Σ��߹���ʱ̫С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ⶵĴ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ʱ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õ�ϧ���ǣ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δ�ܰ����IJ��ܺú�ʩ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Ϊ�������ʩչ���IJ��ܣ�ȴ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ժ�ԡ�Ӣ�š�2001.7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ة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1905��11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㽭���ݣ��漮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8���뺼�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�飬14�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1923����ѧ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ѧѧϰ��1925���^ת����ѧ���İ�ѧϰ�����С��ҵ��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ӡ���1938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ࡶ�ǵ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㡷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1950��2��28�ղ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