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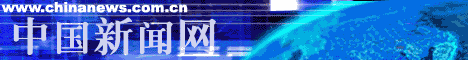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쵽��ʮ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Ͼ͵���ʮ���ˣ�ʲô�о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һ㶣�˵��ûʲô�о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Ӧ�Ƚϳٶ۵��ˡ�ÿ�쿴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ȫ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˪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컹����ʱ���Һ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ۿ���һֱû�н��۵Ļ��⡣ 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ӣ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ȴ�Ĺ����ˣ��ǿ���ô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ؿ�ʼ��--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ɣ�Ҫ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ְҵ�߰ɣ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ĥ�ģ���ʹ���㱾����Ϊʮ���˽���ˡ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ij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Ƶ��뷨����--��һ��ֻ��һ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ֻ�Ӵ���λ���ˣ� 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Ҳϲ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뷨�����ҵ��Ŀ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벻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仯����ʱ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һ�ֻ��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±仯���ˣ���ʵ�ֱ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û�в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ɺԡ����ǣ���ʮ����һ�꣬��ͻȻ�е��Լ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̫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ͺ���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ʼ�į���㣬ƴ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ΰ��Ρ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Ϫˮ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ʱ��һ�ж��Ѿ���ʼ�ˡ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д�˿��б��棬�ƶ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ض���˵���㿴����õĴ��⣬��ô�ѵã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Լ���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ش����ҵ�Ϫ����ɹ̫���ˣ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ǰƴ�����Ρ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֪���ڷ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ȴ�Ӳ�ȥ�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һ���µ���ͨ����˵��һ�ж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ˮҲ�࣬�е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ÿ����ĩ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汼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ʼ��ע���С����С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ڱ�ֽ����ͼ�ҵ�һλ���ʵĴ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˱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Ʒ�꣬ȥѰ�Ҿ���רҵ���ܺͼ�ͥ�ߴ�Ŀ��䡢������ը¯����Ϊ���ҵ�һ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С��ʮ�ҼҾߵ�Ҳ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ĩ�ض�Ҫ������˵ĵط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ģ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Ļ�ɫ�����ָо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ļ�һ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Ϊ����С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ҵIJ�������ԥ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æµ����һ���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䣬�����Ϫ���ı��˷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ǵ�С���ڴ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Ǹ���ȡ���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--�������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ô? 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죬�°���ҴҴҸϵ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·�Ķ��棬ԶԶ���ҿ���ǰ���컹��Щ���ҵĵ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ʰ����Ŀһ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ĵƹ⣬��Լ���Կ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Ӱ��һʱ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ʺͿ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 ���Ҳ�û�����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ȥ��Ӫ���ǵ�С�ꡣ�����ɷ�ÿ�춼�ڵ���æ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ȹ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еڶ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Ѿ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Իؼ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Ĺ�â�����ҵ��ɷ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ſڣ�˵һ��С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ȥ���տ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һ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 �����ҿ�ʼ�����ǵ�С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ӵĸо������ָо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Ц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־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硣��ֻ�ܲ��ϵظ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֣��ټ�֡� ��һ�죬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˳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Ϊһ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ѧʱ��ѧӢ���õ�С¼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Ժܽ��ĵط���Ȼ��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ݱ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"��ԭ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գ�ϣ����һ֧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ȴ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ר��¼�Ƶ�"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"��Ŀ�����Է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ڵذ��ϣ��Ҽ���ɤ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Ŀ�ֺʹ�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ɷ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һ�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Ϊ�˱��˵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ҹ��ֱ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ô�IJ�ͬѰ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缸��ÿһ�춼�ڷ����Ų�ͬ�Ĺ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˵Ĺ���ʹ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б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ҵ���ʮ���ˡ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