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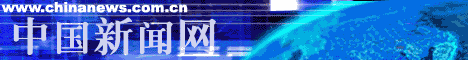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ӡ���ס�ڲ�����¬���ִ�ѧ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ʯ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Ů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Ȼ���ǵ���̬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ڴ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ݸ��һЦ����ʾ�ø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ﶼ�ǽ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û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ᡢ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ڴ���ϣ��ȱȽ��ǣ�˭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һƬ�հף�����˵��һƬ�հ��Ρ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İɣ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λ��Ů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"Ϊʲô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 ����Ҫ��Ū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ȵ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 �����ӱ��濴���µ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롣��άҲ�ɺ��ѿ���һ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¥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ʷ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ͳ��й����Ĺ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߹�Ĺŵ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Ĺ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Ϊ��Ƭ�ϱ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ʶһλʫ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ͷ�β���ʫ�˶���ijij�������ᡣ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յĵ۹���Ȼ��̵ػ��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۹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Щ�ϸ��ˡ����Ǵ��ų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Ͱ͵�Ƥ�⣬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Ĵ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˿֯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ڵ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߹�ȥ������վ�Ų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�ȣ����Ź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Ҳû�У�ȴ�ѱ��ֳ�����Щȱ�������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ﻹ�ܿ�����ص��Ĺ���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ʷ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磿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ص���ʷ�Ļ���Χ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ͳ������֮ҹ�����Ҹ��Ժ��һ�λ������衣Ʊ�۵İ����Ʊ�ļ����Բ���˵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һ�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㡣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ϵ��Ŷ��ݻ��İ�ɴ��ȹ�����Ҹо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졣����һ�𣬱���ͬ��Щ����ɫ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һʱ�������糡�����ٸ�ѩ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׳����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顣�˿̣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ԵĹ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ؾ���--���Dz����Ǿ���Ļ����أ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Ҳ�ɵĹ��Ҹ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˭˵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˭˵������ò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ʩ��ħ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ı��˵�һ�У� 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µ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һ��С�ƹ����ֻҪ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䣬Ҳ�ܸ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ͣס��һ֧�������һ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ظ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ƹݵ��ˣ���Ů���٣���ͬ�ϰ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˸߲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糺죬�����㵸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Ƕ���˾ơ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裬�ȾƸ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һ�С� 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ǰ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Щ�Ű���ϸ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վ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𣿵�Ȼ��-- ����άҲ��ɭ�ֱ�Ե����С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ʾӣ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·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ء���С·�ͱ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С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άҲ�ɵ����˳���ɢ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ȻҲʱ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һ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ӵ�ŵļⶥľ�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ɸ�����Ĺ�ߣ��ڵ����ζ���ż��һ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ζ��·��Ϫˮ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Ҷ�䣬һ��һ�𣬻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˺���ͣס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ٿ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ǹŰ�֮��һɨ���գ���˸˸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ɶ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ɹ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겻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ժ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