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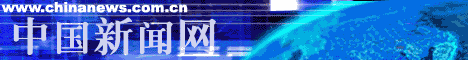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û�з羰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Ӱ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ͬ�����롣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Ȯ���ŵ�С�ӿ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Ӹ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о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ı�Ե�ռ����صػ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ĵ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ĽŲ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й��İ�ͼ�� ��Ӱ�����η����Ź�ͬ�����룺���ɡ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ռ䣬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ռ��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��Ŀռ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ص㣬�ص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Ҫ�е����壬���߸���ɫ���� 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û�к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е��й�����һ��û�з羰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Ƭ���Ǽ�¼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š� ���ǵij��в����ִ���ҵ��ģ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ǵĹŶ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Ҳ���Ǵ��ӵ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ǵĵ�Ӱ�У��й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ͱ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š��й����ǹ�ȥ��δ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ֻ�йؼ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ǰ��Ȼ���й���ŵ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ɻ��ش�Ժ��ҡ�����ꡢ���塭������һ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ɡ���Ϊ�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С�Ҫ��һ�仰�����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͵ģ�����ֻ��д�¹��ڱ����Ĺؼ��ʡ� �ഺ �������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ɫ�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ഺ�ij��У���Ұ��Ҳ��˳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01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廪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㡶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ӡ�ʱ��101��ѧ��У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غͳ��ӹ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㣬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ոտ�ͨ���廷��Ф�Һ��Ŵ�101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ﱾ���ǵ��͵ij����ϲ���ֻ�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Ƨ������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10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 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dz��˾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켣�ڱ����Ĵ��С��ⲿƬ����һ��ɨ�����쾩�Ƿ�չ�ľ�ͷ�ٶ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ʳ�á�ũҵ��ѧ��У����ҹ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غ�������1996��1997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ϵĴ�仯�����ⲿ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ֱ仯�� ����һ��ħ�õľ���֮��б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˧�ġ�ʮ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һ�ݿ�ݹ�˾��ְҵ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Ϳ�ݡ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ӰƬ�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ᷢ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ij��У��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֪���ø��ࡣ 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ij��У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ĵ�Ӱ�У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κ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ٶ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飬�ഺ��Ʒ���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͵ij��С� �㳡 �������𱱾����㵱ȻҪ�����찲�Ź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߽����ǴҴҵ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ġ��㳡�������ⲿӰƬ��찲�Ź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�Ҳ�ܸ������ĵļž����찲�Ź㳡�ھ�ͷ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Ա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Ⱥ�ù㳡�İ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һ�����°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ķ�ܴ�Ҳ�в����⾰���찲�Ź㳡���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㳡�ϵ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ͬ 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ڹ�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�SOHOһ�壬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ꡣ������ռ�ݺ�ͬ���Ļ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Ǻͺ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֮ǰȥ��ͬת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Թ�һ�����ϳǺ�ͬ����ҹ֮����Ȼ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ǵĺ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Ը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Ժ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Ը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ʵ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ҡ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˼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ֻ��ä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Ʈ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Ը���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Լ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ĵط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¼Ƭ�˶������硢����Ӱ��ļ�¼Ƭ�ͽС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ä��"��Ƭ�ӵ�5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ä��"�ŵ�ʫ�ˡ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ĩ�ң��ڹ�ȥ��δ��֮��Ļ�ɫ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Ϊ�ҡ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˹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4��ǰ�ļ�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껪ȴ��ˢ��һ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Ĵ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пռ������ڸֽ����ܵIJ�����¥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˸��֣�10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ڳ��Ų�����ϸ裬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--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С˧������ѧԺ�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ѧԺ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ŦԼ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أ�����ѡӢ���㲥��˾�����Ӱʷ�ٲ�ӰƬ֮�С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䡷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23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94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졷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ȫ�й���Χ�ڵ�ҡ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Ҵ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ĺܶ�Ʈ�㺣�⣬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ɢ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ͨ�غͲ�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һ���ޱߵ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еĵ�̨���ַ��ϳ���Ȼ����лĻ��ȥ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¼Ƭ�Ĵ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Ƹ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ݺ��ӵ�ע�š� ��ۣ���ĺ�˼� �����仨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һ�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䡣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ҡ���Ӱ�е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컡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"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̳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Ӧ���dz�ĺ���ι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۾ͳ��˾���ľ���ȥ�ƺ�Ҳ���С� 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Ӱ��С�䡷����Ӱ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ڴ�½�����֮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ݲ�ͬ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ǽ�ˮ¥̨�ȵ��¡� �ڳ¹�֮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Ľ�ͷ�����ǻʺ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dz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ػ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էһ������IJ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֮�飬������Ǵ�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֮�鲼���˺۵���һ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ر��Լ��ľ�¥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̴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˼�ʻ�ش���ɫ�鳡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𣬱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͡�����ƮƮ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ں���ʹ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ܣ�Ī���Ŀ�ʼ��Ī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˸С� ����97֮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½���ε��ȵ㡣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ֻ�ǻ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ȥ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̫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ֳ��ʱ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ˣ����ֶ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㡣���ǣ����Ա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 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¦�ǵľ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ݺ�--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£����Խ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仧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ݺӣ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ԼԼ�ƺ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�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֣�ʱ�����ͤ�Ӽ䣬ʱ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ľưɣ�ʱ�����ź��ɹ��յ�ѧ��װ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Ĵ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���ģ����ְҵ�����Ҿ�ɢ���롣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Զ�ı� ���Ϻ�Я����һҹ�����Ĺ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Ǿþô��̡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ҹĴ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Ϻ��ķ绨ѩ�ºͽ�֦��Ҷ����Ч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ײ��С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ϡ� ����2001�꣬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ƵĹ��裺"�Ϻ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黳������̨ͬ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⣻�Լ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о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죬�Ϻ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"�����ƺ�˵����"ϲ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һ�ֵij��з�չ��ս�У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Ʊ���Ϻ��õ����ֽ𡣵�ȷ��APEC��ͽ�����Ϻ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ֶ�½������90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ذεض��𡢴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顢��ï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"��"���飬һ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˶��Ѿ���ʧ�˵���ʵ���Ϻ�̲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·�ͻ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һ�µĺ�ɽ·���ɴ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ո�µľ��·��ƣ��¾ɵ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ȿ��ȵ�����˵�й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裬��̲���Ϻ��Ŀ�����ģ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
��ժ�ԡ�ʱ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