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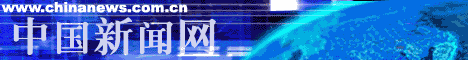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ڹ��"�ɲ�"
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Сʱ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֮һ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װ칫���ϵĸɲ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ĥ���жʱ�丸�ļ���Ϳ���"��"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쵼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Ǵ�Ժ�V����ߵĸɲ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?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֮�׳����ҵ�ȱ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ʲô�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ע�⡣ 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һ��˺���ѷε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롣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ģ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µĶ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û��ʵ���ҵ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й������Ǿͳ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Ҫ���뵱�ɲ����ܵ��ϣ�����Ҫ�κα��֡�����Сѧ��Ͳ��ܴ����εĸɲ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--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ѧѧ�������ϯ�ˡ�Ҫ���ڹ��ڵ��ɲ�Ҳ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Ҵ��Ҳ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ţ���ĸͨ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--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ӳ�Ϣ��! 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ûʲô���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һ���й�ѧ��ѧ�����ᣬ�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кü�����ϯ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ɼ��ں���ɲ�֮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ѧ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飬ͻȻ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źܶ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л����ѷϳ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죬�����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ϸ�ѧ���ḱ��ϯ��é��绰��"��У��¥ǰ���ҡ�"��é˵�� ����"��У����ʲô��?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?"һ����úܾ��µ�����ʮ��˶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 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̸̸��У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ѷ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Ƕ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衣�Ҵ����й�ѧ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ǿ�ҿ��顣"��éӢ�ﲻ����һϯ��˵��Ů����Ŀ�ɿڴ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ǵķ�ŭ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ɿ����һ��ֽ�����űʼǡ� 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У��ͨ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־塣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ʮ���Ӻ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ܺ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"�Բ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ί�и�У��ղķʿ�����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Ů����˵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ǷǼ�У������!"��˵�� ����"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Dz��ߡ�"��é�ı߹��õú��졣����Ҫ��60����μӹ���Խ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췴����ζ�� 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߽�У���칫�ҡ��ҳû���ȥ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ڽ�ͷ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칫�ң�����é���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ĵ���ȥ��Ů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Ժ��档"У�������ȷû��ʱ�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2�㵽1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ǡ�" �����ҵ�ͷ����éȴʹ��һ���У�˵��"У���ܽӼ������й�ѧ��ѧ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ٶ��ˡ�" 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Բ�����Ҫ��ʾһ��У����" ������é�ܵ���ؿ�����һ�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ϣ�У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Ȼ��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»�ij�Ա���ᣬ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ò�Ҫ����ʮ�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ⲻ���й�ѧ�����һ�ξ��й�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ɹ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Ϊ�ѻ���У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֤��һ��Ŭ����ǿ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⽻����֪ʶ�����ٷ����ƵĴ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é��ԭ�ŷ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ǽ�ϣ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һ�ű�ҵ֤�����ǰ��Ÿ�ӡ�˸����¹ݼ�ȥ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ν�--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ѧ���ᾭ�ѡ� ������é"�ʼ�����"��ͼ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ũ���г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û�гɹ������ô�Ҳ�Ҫȥũ���г���˵ĺ��ٲ�û�еõ���Ӧ--�Ƕ��IJ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ұ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ηŵ�Ӱʱ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ܵ��ڳ�ͬ���ij�ʱ��Ĺ��ơ��һ���֯��һ�ν��κ�Ұ�ͣ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ܻ�ӭ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ӣ��ӳ�����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ܳ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û�г���ͬѧ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é�δ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ͷ��ͦ׳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úͲ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é�ġ� ����ε��ɲ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ҵļ����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㣺ÿ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Ҫ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�ס�� ��ժ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ֳɳ����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