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www.johnnytowncar.com.cn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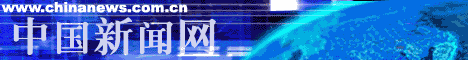 |
|
����Ů�Թ�֮�Ƚ� �� / �� �� 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Pamela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ʵ�е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ר�ſ���ӡ�£�һ������д�żĺؿ�ʲô�ģ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µظ��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˸��й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ȶ��й���һ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ҵ�Ȼ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ﲩ�����¸�ʲô�ģ���ʹ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"Ϊʲô���ǹ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Ů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Ҳ�����ư��Ƶ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Ĵ𰸣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Ƶ��ͷ��ʱ��Ӷ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һ���£����Һ��и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ΪŮ����һ���й���ķ����淢��ȥ��ӦƸ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Ƹ�ߵ����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Ⱥܾ��ȣ���ΪҪ����ķ���кܶ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ƴ�ѧ�ı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˼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һ��ȴ���ɷ����ģ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λ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ڴ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�֣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ͬ���𣿱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Լ�Ҳ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ס�"Wait a minute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ȴ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ͣ��"Where am 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ʲô�أ��й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죬����ͬ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ǻص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Ͳ�֪��ɷ�˶��ٻ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еĸ�����Ů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ձ�Ůͬ�£�����Ϊ��Ľ�й�Ů�˵�"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й����˵Ŀ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롣�Ͼ���Ů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ȣ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Ծ�Ϊǰ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Ůƽ�����ⲻ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ˮ�л�����һ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˵��һ����û�д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ձ�Ů�ӡ� 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ν��ŮȨ������һ֪��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ζ���ѧ�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�ʷ�Ϻպ�������ŮȨ�����ߵ�У�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һ��ŮȨ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צ��ʲô�̶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ϣ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ŵ��Ǹ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̫̫�����Ҳ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е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ᶨ��һ���Ҳ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Ц�ĵ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ἰ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س���һ����ԭ��ŮȨ������Ҳ�ǽ�����ӵģ� 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ĸϵ����"��"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о�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���ΪŮ�Ե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Ǿ�"Where am I ��"��ȴ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Һú���һ�룬��ΪŮ�ԣ������̶ȵ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˭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Լ��װ���ĥ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Ļ���ͳ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˵ij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Եģ�������ŮȨ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ľ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Ů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Ů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Աȸ��ˣ�"Ůǿ��"�ı���Լ�Ůǿ�˱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ϵ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"��Ů�Զ�λ����ʵҲ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Ϊʲô��ô˵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͵��㿷֮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ԩ�飬������Ůǿ�����ļ�ͥ�ջ��Dz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ȶ���ͥ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Ҳ�dz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ȫ�У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ź��ɷ��ϲ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ǵ���һ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߳ɾ͵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ϵ����һ�ݰ�ȫ���أ�Ҳ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ļ�ǿ����һ���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ڹ�ϵ����Ҫ�Ǽ�ͥ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κ�һ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е�˫�����Ե��Գ�һ��ij̶ȣ��ɹ��Ļ����Ǹ߶��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ϣ���Ϊ�˱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廯"���ˣ��Dz��ܼ�ϣ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һ����ʵ�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ͥ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ڼ���̭�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ǵĻ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ΪŮ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ֲ���ƾ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͵��˵ģ�����һ�㣬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"���ܸ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ĸ��˷�չ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Թ�ϵ�ʹ�"���չ��ң����չ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"Ϊ�˱˴ˣ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չ˺��Լ�"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Ͷ��и���İ�ȫ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룬�й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ʵ�Ƕ��˶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洦�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Ů�ˣ�Ҫ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ʵ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в��ٹ̲��Է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þ���ģ���ž�Ҫ����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ˡ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˵��Ե���ʱ����Ů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ģ��ɲ�֪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ֻҪһ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ˣ�ȴ��Ȼ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˵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ʱ����ݻ����ִ��İ汾��֮һ���ǣ�"���Ӷ���ô���ˣ��һ��w�w���˴�Ӧ������ʣ�ʲô�w�w�w���˴�Ӧ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أ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Ķ������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ѧ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Dz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˵������"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Ů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в�"����"��Ů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Ҳ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ʹŮ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ӯ--��Ϊ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ģ���Ϊһ��ĸ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--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ǵ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䣺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ȫ��һ��Ů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Ů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һ��"����"���й�Ů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ʣ�Ϊʲô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˻��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ѵ�û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"˵ʵ����֮���Լ�ס���ϸ�ڣ�����Ϊ�ҵ�ʱ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룺�����ǰ��黹�Ǵ�ŮĤ��ȫ��һ��Ů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Ҳֵ��ͬ����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̥ʮ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Ա�����ȫһ��Ů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ʶ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һ��ʲô���ĺ��ӻ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Żŵ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ȥ�й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ܶ�Ҫ����һ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ȵ���δ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ҿ�ʱ���˷ܵü���Ҫ���ˣ�"Beautiful��Beautifu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Ƭ��ס�ڵ���̾�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Ե�Ϊ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й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Winni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ȳ��˺����Ѻ�Winnie�ɳ��е�����ϸ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Ͼ����й�Ů������Winnieÿ�μ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һ�ֱ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˻�ĸ�ס� ������һ�Σ��ҵ����Ҵ��ţ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Winnie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챨����ҿ�˵��Ҫ��Winnie�ղ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ҴҴҿ���һ�ۣ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ಡ"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ֽ����ø��ҿ���һ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ԥ��Ҫ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е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ֻ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ĸ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õ��й�����Ҳ�˲��ϳԣ������ʹ�Winnie���ȥ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Ĵ�ë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ź��ӳ��� ��ë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˵ʵ�ڵģ���һ���ӣ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ھΣ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ο�ң�˵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ƾ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̲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㲻��Ѻ������˻�ȥ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м���Winnie�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ʱ��֪�DZ���ϲ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Winnie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Ӿ�ģ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һ���쳤��Ҳһ����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Ҳ��ůů�ġ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ȵ�email˵����Ҫ���й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ΪWinnie��һ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Ҫ��Winnie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ϼҿ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һ��Winnie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䡣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Ը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й���Winnieǰ����һֱ��ĥ�Ÿ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Ů����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email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ɺ���һ�ᣬ�뵽Winnie�������ܻ��淴�����ܻ�Ϊ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Щemial�������м俴��һ��Ů�˵�ĸ�ԡ����ͷ��ס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ѪԵ��ʹ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ճ�Ϊĸ�ġ�
|
|
.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㡣 |